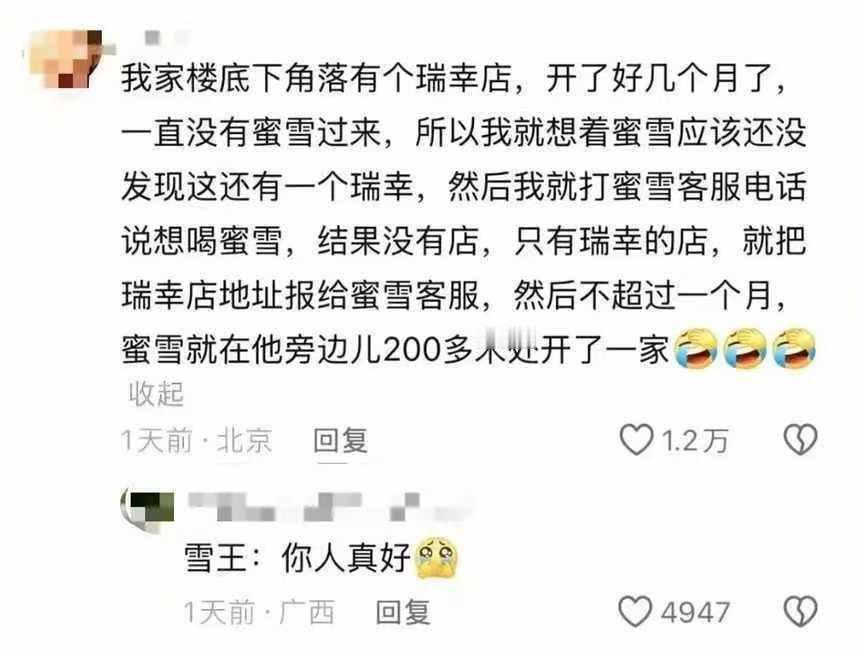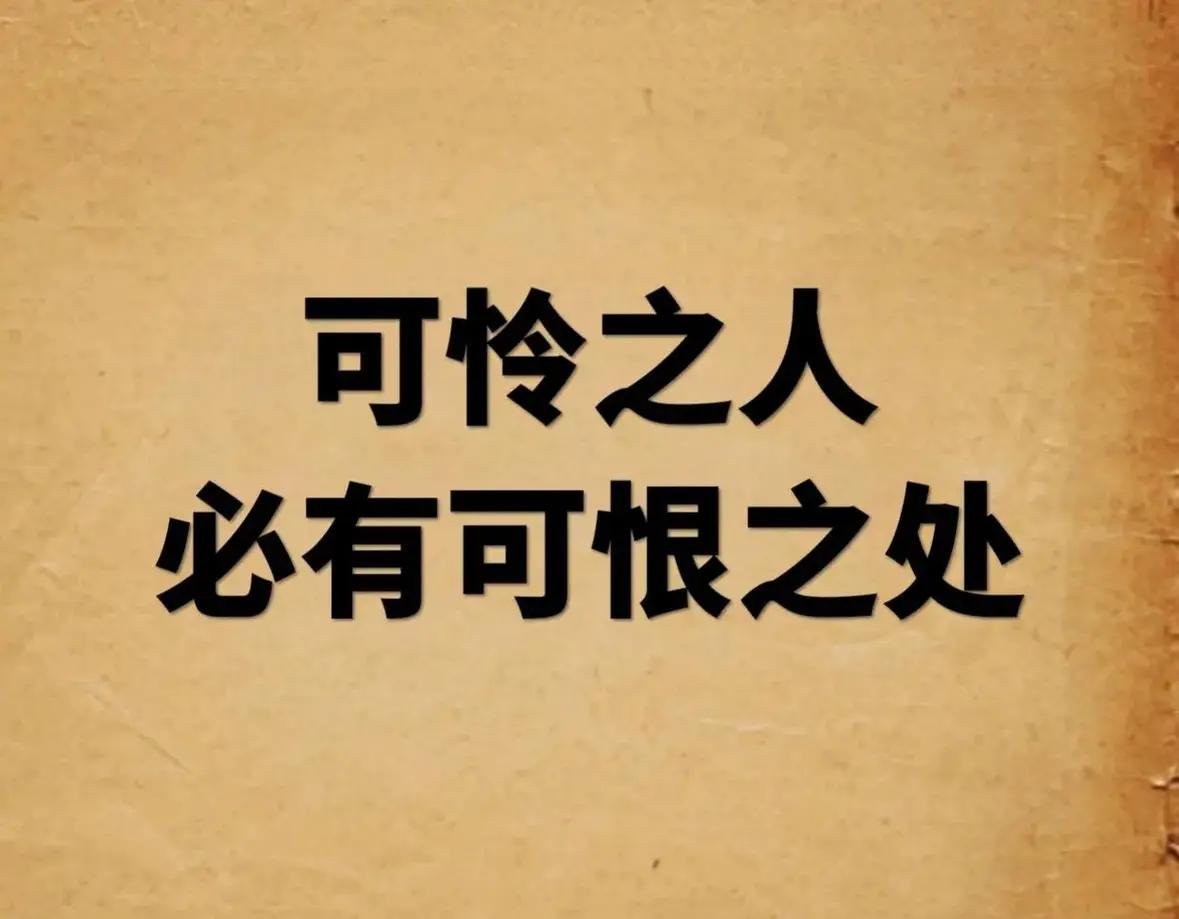刘墉告老荣归,途中遇千总无礼喝止,他从容取出名刺,千总瞥见。 那千总凑近一看,名刺上只端端正正两个小楷:“刘墉”。这名字像块烧红的烙铁,烫得他眼皮一跳。方才那副跨刀而立的威风,霎时间泄了气,脸色由红转白,又由白转青,喉结上下滚动,半晌挤不出一句整话。他哪里想得到,眼前这位布衣老者,青衫简从,竟是朝野皆知、天子敬重的老相国。 官道上顿时静得只闻秋风扫过车帷的悉索声。随行的几个兵丁面面相觑,不知自家大人为何突然成了泥塑木雕。刘墉倒不以为意,将名刺缓缓收回袖中,嘴角仍噙着那抹淡然的笑,仿佛刚才不过是被问了个路。他轻轻掸了掸衣袖上并不存在的灰尘,目光越过呆立的千总,望向远处蜿蜒的官道,那儿正通向他的山东诸城老家。 这小小插曲,像一粒石子投入古井,在刘墉心里却没激起多少波澜。宦海沉浮数十载,比这大得多的风浪,他见得多了。乾隆朝那么多能臣干吏,起起落落,能在中枢屹立数十年,伴君如伴虎而终得善始善终的,屈指可数。他刘墉靠的,从来不是疾言厉色,不是煊赫威权,正是这份“从容”。这份从容,是阅历磨出来的底气,是智慧凝练成的静气。 遥想当年在江宁知府任上,面对盘根错节的江南吏治,他没拍过惊堂木骂过人;后来督察漕运,整顿积弊,多少豪强暗中使绊,他也没见疾言厉色。父亲刘统勋一生清刚,如同挺拔的松柏,风雪摧折而不改其直。刘墉则更像一块润泽的玉石,外圆内方。他的原则藏在心里,行事却讲究方法,懂得审时度势,和光同尘。他知道,许多事情,硬碰硬反而办不好,就像治水,宜疏不宜堵。 那千总终于回过神,腰杆弯得几乎要折过去,脸上堆满惶恐与谄媚,连声道:“卑职有眼无珠,冲撞老中堂车驾,罪该万死,罪该万死!”声音都打着颤。刘墉这才微微转回头,看了他一眼,语气平和:“不知者不罪。你履职盘查,原是分内之事,何罪之有?只是,为朝廷守关隘,查奸宄,眼要亮,心更要细。不是看谁的车马鲜亮,谁的随从众多,也不是看谁布衣陋车,便可轻慢呵斥。百姓敬我们身上这层官服,我们更该敬‘道理’二字。今日是我,若真是位有冤情、有急事的寻常老者,你这般做派,岂不寒了人心,也污了朝廷的体面?” 几句话,不高不低,不温不火,却像鞭子轻轻抽在千总心上。他额头冷汗涔涔,连声称是,心里那点仗着品级、在地方上作威作福的得意,被剥得干干净净。他慌忙喝令兵丁让开道路,亲自搀扶刘墉登车——虽然刘墉摆摆手,自己稳步上去了。车轮重新转动,千总还领着众兵丁垂手躬身,站在路旁,直到车队远去,变成官道尽头一串小小的黑点。 车厢内,老仆一边给刘墉斟上一杯暖茶,一边还有些忿忿:“老爷也太好性儿了,这等轻狂无礼之辈,合该好好训诫一番。”刘墉接过茶,揭开盖碗,轻轻吹开浮叶,抿了一口,才缓缓道:“训诫,不是靠官威压服。你看他方才颜色更变,是真知道怕了。怕我这张老脸,怕我过去的官职。但这‘怕’里面,有几分是明白了道理?我点他两句,他能听进一两分,日后对待百姓能稍存一分敬畏之心,便不算白费口舌。若摆出宰相架子,痛加申斥,他当面磕头如捣蒜,心里只怕怨气更深,回头变本加厉,还是百姓遭殃。我们回去做老百姓了,更要给‘官’字,留一点该有的样子。” 老仆默然,细细品味着这番话。车窗外,田野平旷,秋收已过,大地显出一种坦荡的苍黄。刘墉望着这片生于斯、长于斯,如今终将老于斯的土地,心中一片澄明。荣辱也罢,显赫也罢,都像车后扬起的尘土,终要落定。重要的是,这一路走来,是否守住了心里那杆秤,是否对得起“读书人”三个字。为官,他力求上不负君,下不负民;做人,他但求内不愧心,外不愧人。如今跳出局外,回头再看官场百态,更像看一场大戏,台上人演得热闹,台下人看得分明。那些刻意张扬的,往往跌得最快;而懂得收敛锋芒、心存敬畏的,反而走得长远。 车队稳稳前行,故乡的轮廓在暮霭中渐渐清晰。刘墉知道,等待他的,将是另一种生活,烹茶煮酒,课读子孙,与乡邻闲话桑麻。至于官道上的那次邂逅,不过是漫长归途中的一丝微风,连涟漪都未曾多留。但他希望,自己那几句平和的话语,或许能在那个千总,以及更多偶然相逢的“为官者”心里,种下一颗小小的、名为“分寸”与“敬畏”的种子。这或许比任何雷霆之怒,都更有力量。 夕阳给车队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刘墉的脸上,舒展着真正的平和与安然。他的故事,不在史书的轰轰烈烈里,而在这些归途的尘埃与对话中,凝结成一种穿越时光的智慧与温度。 【本文历史背景与人物言行细节,参考《清史稿·刘墉传》、《啸亭杂录》等清代史料及可靠笔记文献,结合清代官制礼仪及社会风貌撰写而成。】
2002年,一个武汉女大学生被老师追问,是否跟黑人留学生发生过关系。女生羞愤不已
【38评论】【7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