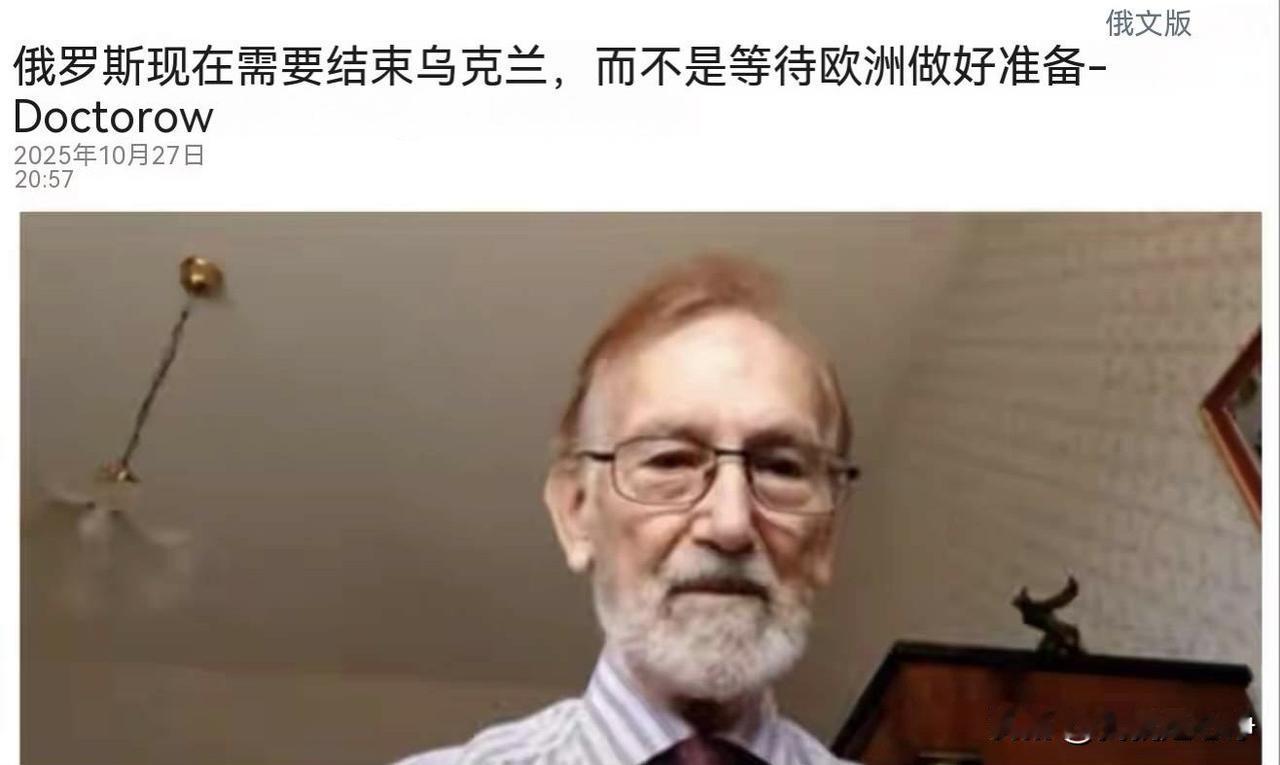马凯硕有信心的地方,也正是我最担心的地方。 他认为,印度领导人始终保持清醒的战略头脑,在面对美国、俄罗斯、中国时都能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去思考。他又以欧洲作为反面教材,认为欧洲领导人的政治水平已经大大退化,欧洲在未来的世界中只会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 印度这种冷静算计的特质在其对美政策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尽管美国极力拉拢印度以构建所谓对抗中国的联盟,但新德里方面始终保持着令人惊讶的冷静。 马凯硕看得透彻,他明确指出印度渴望在一个多极世界中作为一个独立的极点崛起,而非成为谁的跟班。这种独立自主的倾向根植于印度的大国雄心,其总理莫迪更是公开点明,印度的“真正敌人”并非某个国家,而是对外国的依赖本身,从而大力推动“自力更生”战略。 即便在2020年边境冲突后对华情绪转向负面,马凯硕仍提醒印度,在地缘政治中情绪化的一方往往是失败者,重要的是冷静盘算国家利益所在,并非只能在“仆人”和“敌人”之间做极端选择。 他甚至建议印度效仿中国历史上“韬光养晦”的智慧,避免地缘政治对峙,集中精力发展经济,因为时间站在印度一边。 对于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这类能深度融入区域经济的事务,马凯硕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度的犹豫是一个战略失误,作为印度的朋友,他坚信印度最好的选择是立即加入并与东亚国家深化经济合作。这种立足于长远经济发展而非短期阵营对抗的思维,正是印度战略理性的核心。 然而,当视角转向欧洲时,马凯硕的观察就充满了失望。他认为欧洲正陷入一种“战略幼稚病”,其领导力显著退化,在地缘政治棋局中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种退化首先体现在欧盟核心引擎——法国和德国的失灵上。 当前,欧盟正面临关键时刻,但法德领导人却因国内政治困境而日渐式微,有分析指出其内部政治危机正侵蚀着欧洲战略自主的根基,导致欧盟整体行动力下降。 马克龙和朔尔茨在国内被各种问题缠身,一位被形容为国内“动荡”占主导,另一位则面临“瘫痪”的政府,这使得欧洲在需要凝聚力量时却难以形成有效合力。 更致命的是欧洲在战略上的短视和对外依附性。马凯硕犀利地批评布鲁塞尔已经盲从地追随华盛顿太久了,以至于忘记了如何推进自身的地缘政治利益。 这种依附在特朗普宣布重返白宫后显得尤为危险。欧洲人曾坚信美国是完全可靠的盟友,尽管已有特朗普第一任期的前车之鉴,马凯硕认为这种将自身安全过度寄托于一个奉行“美国优先”且政策不可预测的美国的想法,暴露出欧洲战略思维如“婴儿般幼稚”。 欧洲的真正长期噩梦并非东方的俄罗斯,而是南翼非洲的人口爆炸及其可能引发的移民潮,但欧洲却通过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这进一步显示了其战略上的不成熟。尽管部分欧洲政治家开始反思遭受侵蚀的欧洲主权,希望成为国际格局中的独立一极,但由于美国的裹挟施压以及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欧洲战略自主的探索注定道阻且长。 将印度与欧洲并列观察,马凯硕描绘出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印度的行为模式体现出一种古老文明的战略耐心和务实主义。 它明白自己的份量,也清楚自己的目标,因此能够拒绝成为美国印太战略中那个“可靠、顺从的盟友”。 马凯硕相信,印度政府很清楚他们本身就是一个足够大的国家,应该保持独立。相比之下,欧洲则因内部政治领导力有待凝聚,陷入了情感与理智的撕裂。 情感上,欧洲的心和美国在一起,因为他们同属西方文明;但理智上,欧洲人已经意识到,他们对中国的利益诉求与美国不同。 例如,促进非洲的经济发展符合欧洲的利益,而中国是非洲最大的单一投资者,欧洲本应在此领域与中国合作。 马凯硕对此开出的药方是,欧洲必须大胆考虑一些“未曾设想”的选项来重获战略自主。比如,可以威胁退出北约,以此作为迫使美国尊重欧洲的筹码。 或者,与俄罗斯进行新的战略大谈判,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因为从长远看,当俄罗斯与一个获得战略自主的新欧洲重新建立起某种战略互信之后,乌克兰将逐渐成为连接欧盟与俄罗斯之间的桥梁,而不是争议的焦点。 最重要的是,他建议欧洲与中国达成新的战略契约,因为中国可以帮助欧盟应对其真正面临的长期地缘政治噩梦:非洲的人口爆炸问题。 归根结底,欧洲需要效仿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宣布从此将自身利益置于首位,成为世界舞台上一个战略自主的行为体。这条路虽然艰难,但欧洲战略自主之路其实就在脚下,关键在于汇聚共识、向前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