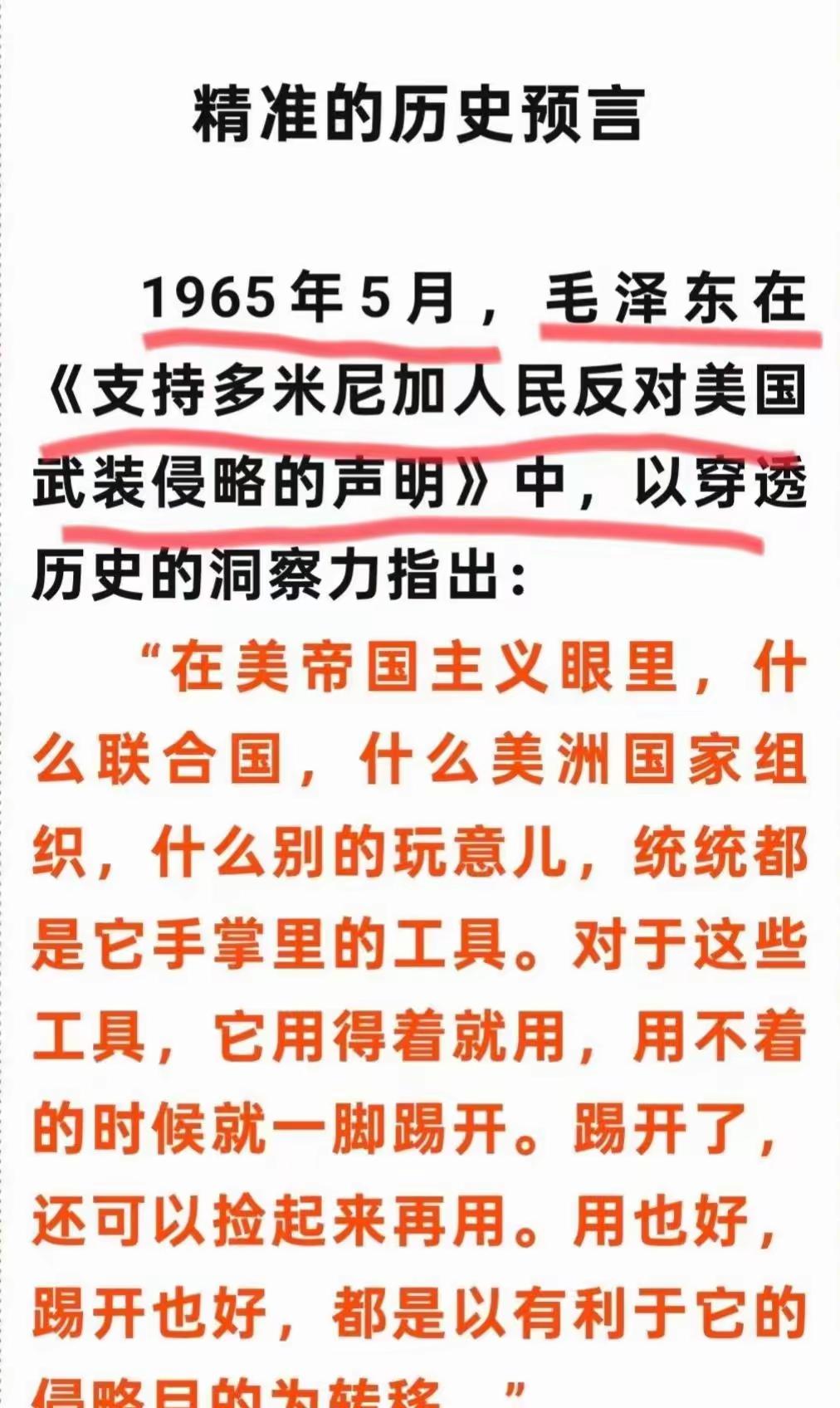1976年,毛主席过的除夕,晚餐就是一条鱼,没吃几口便不吃了。晚年的毛主席,很孤独,常常流泪。 1976年,毛主席过的除夕,桌上就一条鱼,他夹了几筷子,又放下,说了一句:想起全国还有那么多人连肉腥都闻不着。饭桌一下子凉下来。这一句,看着像随口感慨,更像是个老人把一辈子的账又翻开了一页。 那会儿,他自己也浮肿得厉害,手指按上去一个坑,半天弹不回来。厨房想多添两样荤菜,他摆摆手,说一日三餐这样就挺好,中国不缺他这几口。 工资从六百多降到四百多,是他先点头的。出门开会,在人民大会堂喝茶,也得让吴连登去结账。 小灶只认他一个人,亲人都去中南海食堂排队,有人想蹭,他一句话压回去,意思很明白,人民给的那点照顾,只算在职务上,不算在家里头。 屋里翻开看,好东西不多。出访苏联的大衣和帽子挂在柜子里,回国后几乎没再穿。床是木板床,半边堆着书,半边铺着毛巾被,没有棉被,毛巾被一层压一层,有一条上头七十来块补丁。枕头是宋庆龄送的鸭绒枕,靠背垫着长征时带出来那条旧毛毯,他总说留着顺眼,也提醒自己别忘了是怎么熬到今天的。 外人记得的毛主席,多是城楼上迎风一挥手的模样。 晚年坐在床边翻书的时候,安静得多。一九七五年夏天,白内障刚动完刀不久,医生唐由之进屋看他,见他戴着眼镜小声念词,念着念着声音断了,人先抖起来,接着放声大哭。 唐由之一看,他手里拿的是陈亮的念奴娇。词里说的是兴亡,他脑子里跳出来的,很难不连到井冈山、长征路、解放战争里那些倒下去的名字。 书信也能戳到他。 一九七二年,福建莆田的乡村教师李庆霖给他写信,说在农村插队的儿子日子太紧,当父亲的心里发慌。那封信不华丽,却把基层人的委屈写得直。 毛主席看完掉了泪,没有让秘书套话回一封,而是把信压在案头,一看再看,后来自己说,总共看了三遍半。拖到一九七三年春天,他才提笔回信,寄出三百元,说聊补无米之炊,又加一句,全国这样的事多着呢,得统筹去办。从那以后,他嘴里那句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更像是对着一张张具体的脸在说话。 对普通人落泪,对天灾人祸更是受不得刺激。 一九七五年河南南部暴雨,不少县被淹,简报送到中南海,工作人员在床边念到已经死了人,被窝里的毛巾被跟着一抖,眼泪就滚出来。 过一阵,他轻声叨咕,说自己年纪越大,心越软。 一九七六年唐山地震,城市一夜之间成了废墟,他那时候靠鼻饲活着,大多时间是半昏迷。清醒的时候还是要看简报,秘书读到损失难以估量几个字,他又一次嚎啕大哭。 这些眼泪绕来绕去,其实都勾着一个心结。 打天下的时候,他一遍遍告诫部队要守纪律,建国以后又一遍遍盯作风。他在延安看到甲申三百年祭,特意印成小册子发给干部,就是要大家记住,打进北京不算完,守住气节才算数。 黄炎培到窑洞里聊天,说起历朝历代兴也勃焉亡也忽焉的老路,那场谈话后来被反复提起。他给出的路子,其实就四个字,人民监督,说白了,就是让老百姓盯着权力看,人人出来负责,党才不容易变味。 新中国成立以后,他盯的还是这一条。哈尔滨、沈阳那次视察,本来安排得喜气洋洋,餐桌上的菜从盘边排到盘中,他脸色一点点沉下去,只留下了一句不要沾染官僚主义作风。 一九五一年底,东北、华北往北京报上来,沈阳不少人被查出有贪污行为,天津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刘青山、张子善贪污触目惊心。 他在批示里用了一个词,贪污浪费的狂澜。 三反五反铺开,被判死刑的四十几人里,就有刘青山、张子善。有人替他们求情,说是有功之臣。他摇头,说正因为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非杀不可,不这么办,救不了后面那成千上万只是在边缘打滑的干部。 外面的风向他也看得紧。 苏共二十大一开,赫鲁晓夫当众翻斯大林的老账,他听到风声,心里直打鼓。在杭州开的那次会议上,他写了几句提纲,说敌人一手打着和平旗号扩军备战,一手举着和平旗号搞文化往来,图的就是慢慢腐蚀人心。他那几年常讲,社会主义国家也有翻船的可能。 后来的事他没来得及看到,苏联的结局倒像是给他做了一回旁证。 所以晚年人前人后那几场哭,很难当成简单的心软。唐山地震的简报,河南发大水的数字,福建农民的一封信,老战友的讣告,甚至银幕上人民解放军整队进城的一幕,都能戳到他心底同一个地方。一个人一辈子拿人民两个字当轴心,到了生命的尾声,最怕的往往不是自己哪一天走,而是这支队伍以后还能不能守住当年的那句誓言。 那年除夕桌上的那条鱼,后来被人提起,说着说着就变成了一个画面。 房间里光线不算亮,床头那条旧毛毯还搭在那里,杯碟悄悄撤下去,他的筷子停在桌边,眼神已经飘出去很远,很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