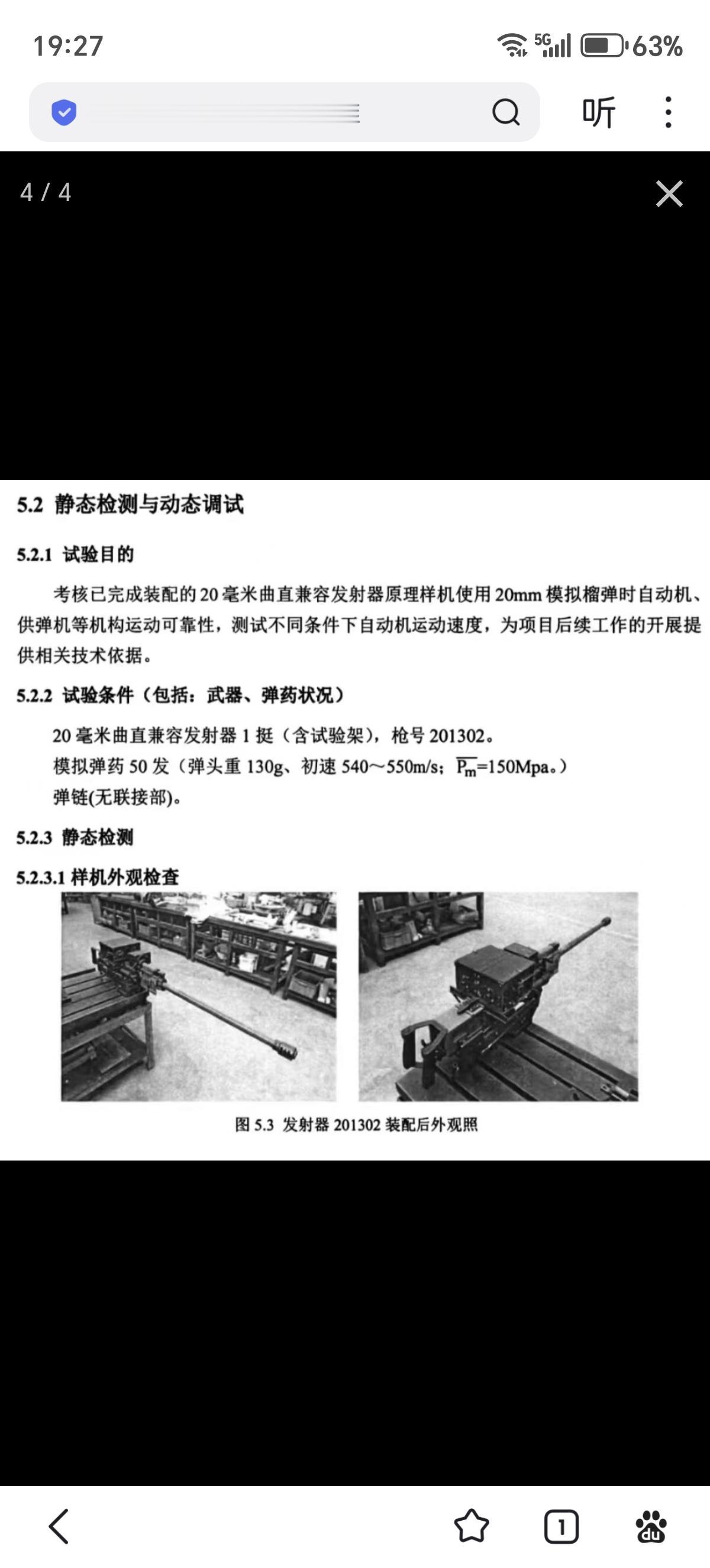1987年1月7日,老山前线。马占福的肚子被重机枪豁开一道口子。肠子流出来,挂在军装上。他用手把那些温热的、滑腻的东西塞回去,用急救包死死勒住。然后抓起爆破筒,继续往前爬。 那是云南的冬天,阴冷潮湿,泥土都带着一股铁锈和硝烟混合的腥气。马占福所在的连队,接到的任务是拿下那个叫“167”的高地。高地不大,但敌人的火力点像毒蛇的牙齿,密密麻麻嵌在岩缝和工事里,压得突击队抬不起头。 冲锋号响了三次,三次都被打回来,山坡上已经倒下了好些战友。马占福是个沉默的青海小伙子,来自互助土族自治县,参军前话就不多,到了战场上更是一门心思。他看见排长急红了眼,看见身边的兄弟一个接一个扑倒,心里那股火就烧起来了。不能这么耗下去,得有人去把那个最凶的重机枪碉堡端掉。 他申请了。没有豪言壮语,就一句:“排长,让我上。”怀里抱上爆破筒,身上多挂了七八颗手榴弹,就和另外两个战友一起,借着炮弹坑和稀稀拉拉的灌木,朝侧翼迂回过去。子弹嗖嗖地贴着地皮飞,泥土溅到嘴里,又苦又涩。 离那个喷着火舌的碉堡还有三十米,最要命的一段开阔地,没有任何遮蔽。一个战友中弹了,另一个被火力压制在石头后面动弹不得。就剩马占福自己。他深吸一口气,猛地滚进一个弹坑,几乎同时,一串子弹追着他打过来,其中一发,就打在了他的腹部。 剧痛瞬间炸开,像有人用烧红的铁棍捅进去又狠狠搅了一下。他低头,看见军装破了,暗红色的肠子混着血汩汩地往外涌。那一瞬间,时间好像慢了。他想起了离家时阿妈抹着眼泪的样子,想起了青海老家那辽阔的、能看见星星的夜空。不能死在这儿,任务还没完成。 这个念头异常清晰,压过了所有疼痛和恐惧。他咬紧牙关,右手颤抖着,一把捧起那些流出来的肠子,胡乱地、用力地往回塞。触感温热滑腻,带着生命最后的体温。塞不回去,就用急救包厚厚的棉花和绷带,在腰上死死缠了几圈,打了个死结。每动一下,都疼得眼前发黑,冷汗和血水糊了一脸。 炸药不能湿。他把爆破筒紧紧护在怀里,用胳膊肘和膝盖,一寸一寸往前挪。身后,拖出一道长长的、触目惊心的血痕。每前进一米,都感觉力气被抽走一分,意识开始模糊,耳边只剩下自己粗重的喘息和敌人机枪单调的轰鸣。二十米,十五米,十米……碉堡里的敌人似乎发现了这个“打不死”的中国兵,火力更加集中地扫向他。子弹打得他周围的石头火星四溅。 终于,到了射击死角。碉堡就在头顶。马占福积攒起最后的力气,猛地站起来,拉燃导火索,将哧哧冒烟的爆破筒,用尽全身力气,从射孔狠狠地塞了进去!里面的敌人惊恐的叫声还没传出来,一声闷响,碉堡哑火了。火焰和浓烟从射孔、从顶部喷涌而出。几乎在爆破筒塞进去的同时,马占福也被碉堡侧面另一个火力点的子弹击中,重重倒了下去。 战斗结束后,战友们找到他。他趴在炸毁的碉堡前,手指还保持着向前伸的姿势,眼睛望着高地顶端的方向。急救包早已被血浸透,变成深褐色。清理遗物时,人们在他贴身的衣袋里,发现了一封没来得及寄出的家信,和一张皱巴巴的五块钱。信上字迹工整,告诉阿妈部队吃得饱穿得暖,让家里别惦记。那五块钱,是他攒下来想给阿妈买件新衣裳的。 马占福牺牲时,只有二十岁。他没有电影里那样的咆哮,也没有留下什么传世名言。他所有的行动,都源自一个战士最朴素的认知:任务比命重,战友在身后,阵地必须拿下。 就是这种朴素到极致的信念,支撑他在肠子流出体外后,完成了那不可思议的四十米爬行和最后一击。他堵住伤口的,是急救包;他堵住敌人枪眼的,是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无比的决心。 今天,我们生活在和平的天空下,很难想象当年南疆边境线上那血肉磨盘的惨烈。但有些东西不该被忘记。不是要歌颂战争,而是要记住,为了这片土地的安宁,曾经有过那样一群年轻人,他们用最宝贵的生命,践行了“寸土不让”的誓言。 马占福,和无数个像他一样的名字,永远定格在了共和国的边境线上。他们沉默地离去,却给我们留下了最震耳欲聋的关于忠诚与牺牲的答案。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