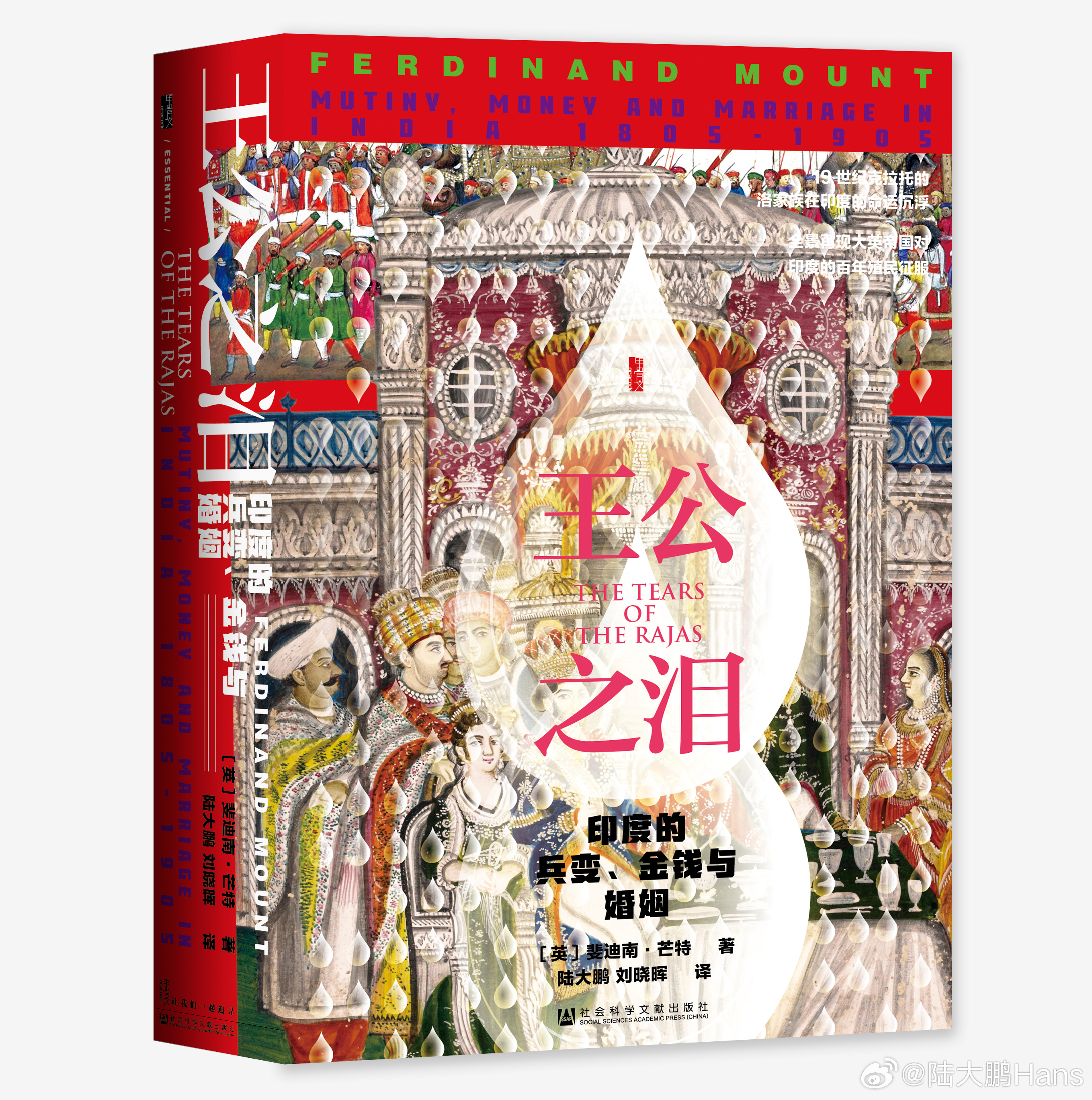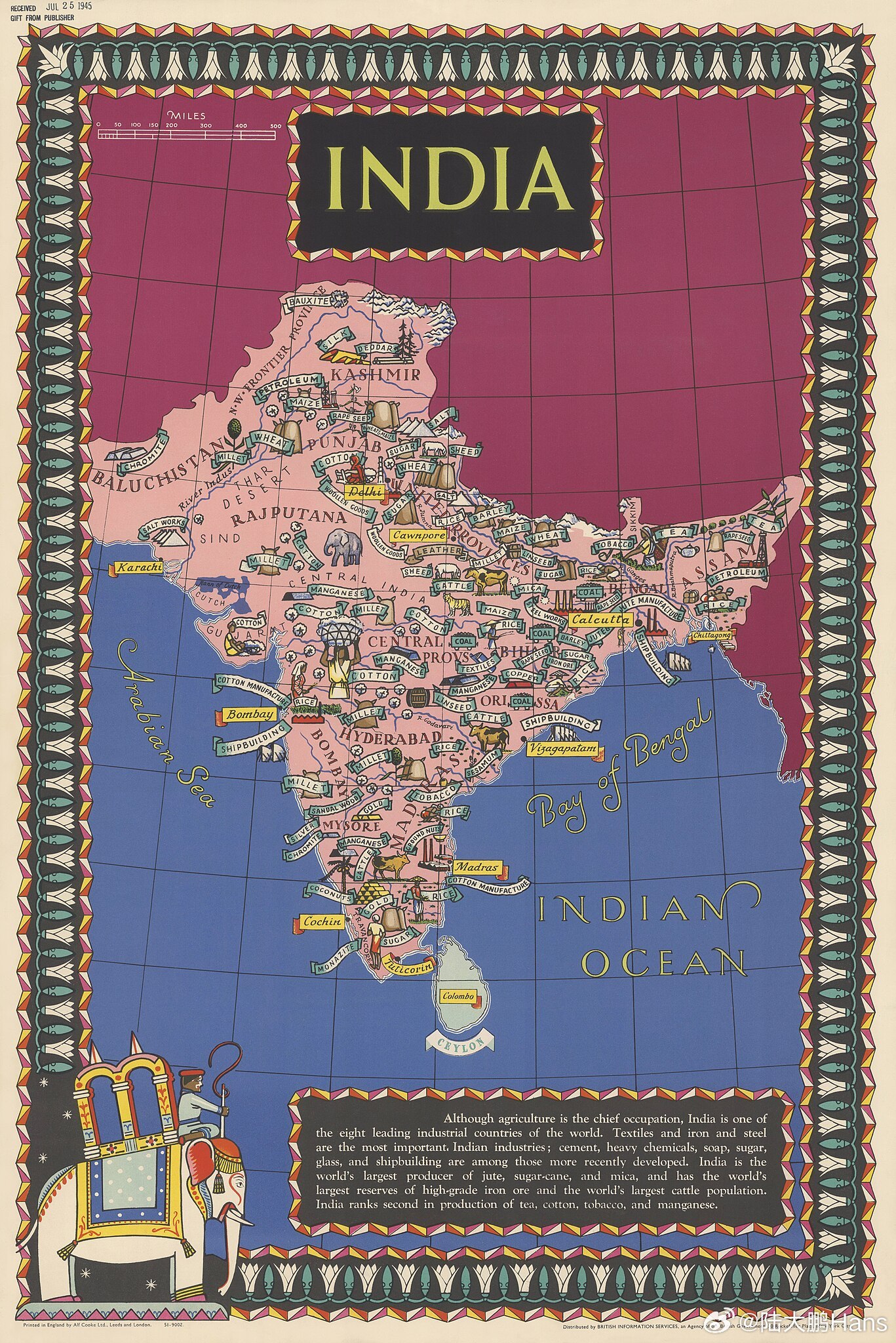鲑鱼洄游一般的生活:18—19世纪在印度的英国人
《王公之泪:印度的兵变、金钱与婚姻,1805—1905》:
他们一连三四代人遵循了这种人生的仪式,毫无怨言,毫无恨意,仿佛完全想象不到别的生活方式:他们至迟到十六岁就离开农场或牧师公馆(伟大的约翰·马尔科姆爵士十五岁就指挥土著军队了),经历漫长旅途绕过好望角,抵达马德拉斯或加尔各答,推荐信,舞会和赛马会,然后是在军营或兵站的孤独岁月,酷热季节在山区避暑地的打情骂俏,寒冷季节里莽撞而凶残的野战军事行动,在驻地教堂举行的婚礼,孩子们在平房 草坪上躺卧嬉戏没过多久就被送回“家”(有时两三岁就被送走,至迟六七岁)去上学,绝大多数情况下直到十六或十七岁才能与父母再次团圆,到那时孩子们也要开始重复上面的流程。这些规模宏大的来回奔波在我们看来就像鲑鱼或燕子迁徙一样不可思议、无法忍受。他们如何能忍受如此漫长的分离?分离的结局往往不是团圆,而是死于疟疾、霍乱、肾病或肝病,或在来去印度的途中死于海难。他们的职业生涯常常受阻,无法晋升,而落伍和不称职的官员拒绝为新人腾出位置。如果他们能活得足够久,得以回国并长眠于诺伍德或切尔滕纳姆 ,还要忍受同胞的冷漠凝视和漫不经心的嘲弄。并且这种生活是多么危险,不仅他们的生命受威胁,他们非常关心的不朽灵魂也会遇到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