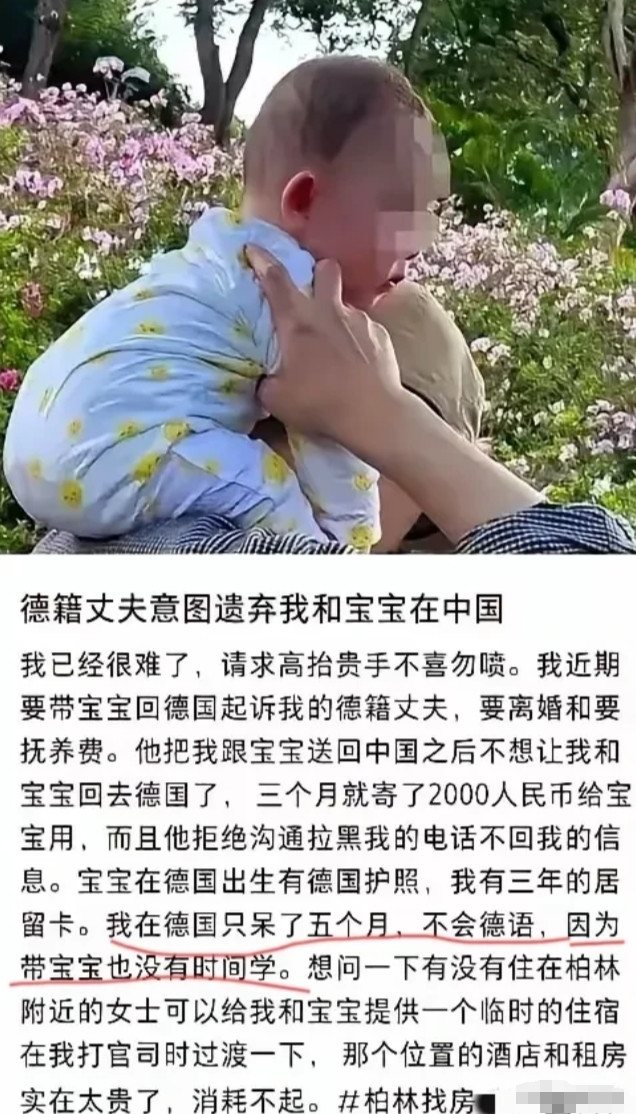1942年,胡琏见妻子独自带孩子操劳,心里动了纳妾的念头,想帮她分担家务。妻子得知后,不但没反对,还把自己的堂妹介绍给他。
重庆的夏天酷热难耐,山城石阶被晒得发白。胡琏站在租来的院落里,看见曾广瑜抱着襁褓中的幼子,还要伸手去拽满地跑的大女儿 —— 她鬓角的头发被汗水粘在额头上,裙摆沾着奶渍。他喉咙发紧 —— 抗战爆发后他常在前线,家中大小事务全落妻子肩上。
“广瑜,歇会儿吧,别累坏了。” 胡琏上前想接孩子。
曾广瑜抬头笑了笑,笑容里满是疲惫:“没事,你难得回来,多歇着。”
他看着妻子憔悴的模样,想起好友的话:“嫂子一个人带三个孩子太不容易,要不纳个妾分担分担?”
纳妾的念头在胡琏心里打转。在那个年代,男人纳妾不算稀奇,但他与曾广瑜感情深厚,此前从未想过。如今见妻子被生活磨得日渐消瘦,他满是愧疚。
曾广瑜出身米商家庭,知书达理,嫁给他后吃了不少苦。娘家破产、哥哥病逝后,她没了依靠,独自撑起全家。
犹豫几日后,胡琏终于开口。他坐在妻子对面,搓着手吞吞吐吐:“广瑜,我想纳个妾,帮你照顾孩子、做做家务。” 说完低头,不敢看妻子反应。
曾广瑜放下针线活,语气平静:“我也正想和你说这事 —— 你常年在外,我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我堂妹曾广仙,比我小几岁,机灵又能吃苦,你要不嫌弃,我介绍给你?”
胡琏抬头,又惊又感动。曾广瑜接着说:“广仙和我知根知底,关系很好,她来了,一家人能和睦,总比找外人强。” 胡琏明白,妻子是为了这个家,才做出这样的决定。
胡琏的婚姻一波三折。第一任妻子吴秀娃是父母包办的婚姻,那时他在陕西农村,听父母之命娶了没文化的吴秀娃。两人没共同话题,除了日常寒暄,很少交流。胡琏心怀抱负,渴望走出农村。
考上黄埔军校后,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在军校里接受新思想后,他眼界大开,再看吴秀娃,觉得差距越来越大。他认为两人没有共同追求,婚姻难以为继,狠下心离了婚。
离婚后,胡琏专注事业。1932 年,他在 11 师任营长,年轻有为,师参谋长曾伯熹注意到他,见他受师长陈诚器重,且一表人才,想把妹妹曾广瑜介绍给他。
胡琏早听说过曾广瑜,她出身商贾之家,受过良好教育,容貌出众,才华横溢。第一次见面,她穿一袭素色旗袍,举止优雅,谈吐不凡,与吴秀娃截然不同。胡琏一下被吸引。
曾广瑜对胡琏也有好感。他穿军装身姿挺拔,眼神坚定,浑身透着军人的英气。两人在曾伯熹的撮合下频繁见面,相处后彼此认定。
1932年,两人结婚。婚后次日,胡琏升任11师66团团长,事业蒸蒸日上。曾家家境殷实,给予经济支持,曾广瑜生活滋润。
好景不长,“七七事变” 后,抗战全面爆发,胡琏奔赴前线,曾广瑜带孩子随家人逃难。日军进犯江西,曾家生意破产。1939年,曾伯熹在赣州病逝,曾广瑜失去娘家支柱,生活陷入困境。
胡琏军饷有限,寄回家的钱不多,曾广瑜带三个孩子在战火中颠沛流离,常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曾经的大家闺秀,如今不得不精打细算,甚至向亲友求助。
好友见状心疼,向胡琏提议纳妾。胡琏本就愧疚,觉得主意不错;曾广瑜历经磨难,也变得现实 —— 她知道仅凭一己之力难撑家,战乱中多一人帮忙,就多份保障。
曾广仙很快到来。她比曾广瑜小几岁,眉清目秀,性格开朗,虽出身没落,但跟曾广瑜识得一些字,性格温顺,手脚勤快。
在曾广瑜的安排下,胡琏与曾广仙举行简单婚礼。婚后,曾广仙敬重曾广瑜,两人以姐妹相称,相处融洽。她主动承担家务和育儿,让曾广瑜轻松不少。胡琏见两人和睦,心中欣慰。
此后,胡琏事业顺遂,升任 11 师师长,屡立战功。曾广仙为他生下四个孩子,人丁兴旺。他对两任妻子一视同仁:曾广瑜是共患难的结发妻,曾广仙是缓解困境的贤内助,两人在他心中同样重要。
战火纷飞的年代,这段婚姻故事格外特殊。曾广瑜不反对纳妾,反介绍堂妹,看似不可思议,却藏着无奈与智慧。 她清楚乱世中独自撑家的艰难,让知根知底的堂妹进门,既能分担家务,又能避免矛盾,是两全之策。
胡琏的三段婚姻,折射出不同人生阶段的选择:与吴秀娃是父母之命的无奈,与曾广瑜是事业爱情的双向选择,与曾广仙是家庭责任的担当。既有个人情感的取舍,也有时代背景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