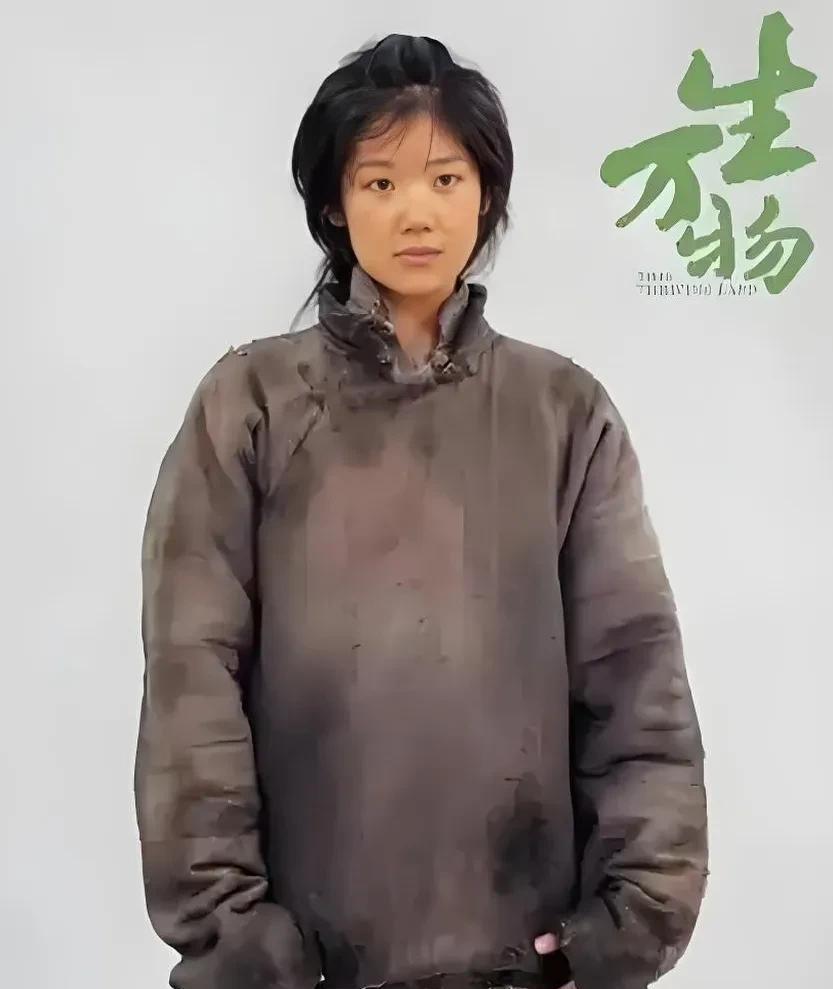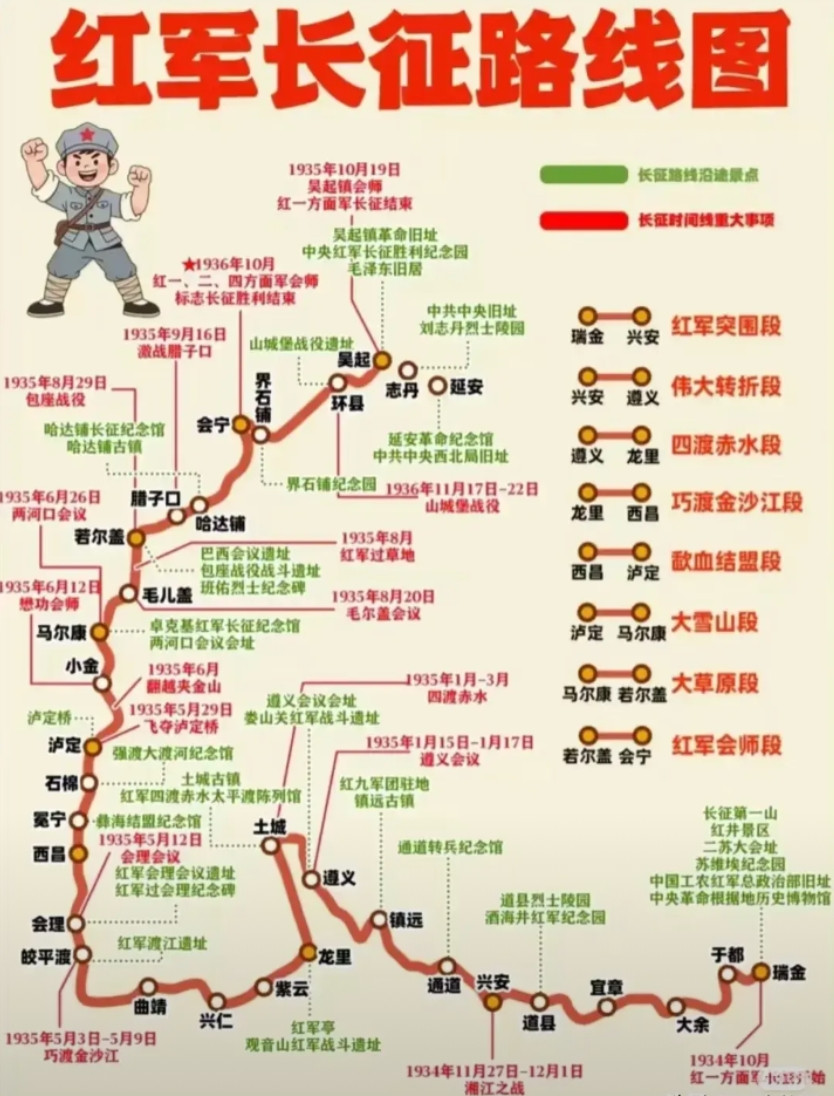明末四十七悍将黄蜚:跨灶之儿,薪尽火传!沉亲裂舰,哑血骂贼! 黄蜚(?-1645),江西南昌人,魁若巨石,刚烈寡言。崇祯六年(1633年)血战旅顺,其舅父东江镇总兵黄龙殉国,以血承继关辽水师衣钵。十年间自守备擢升左都督,太子太保,统摄关辽通津淮海江镇五道水师。麾下辽东旧部操沙船如履平地,裂帆如爪,炮甲覆霜。南明弘光朝倚其为长江天堑,清军斥其为“明末第一水寇”——此獠不死,江海不宁! 这老黄家的热血啊,硬是在一片昏天黑地里烧出了最亮的火星子。舅舅黄龙把命填进了旅顺口的血海,黄蜚咬着牙,默默扛起了关辽水师沉甸甸的旗。他那模样,活像礁石凿出来的人形,石头般硬朗,话金子般珍贵。你说他寡言?那是力量憋在腔子里!十年,从守备到顶天的左都督、太子太保,管着从关外到江南五道水军线,硬是靠尸山血海堆出来的功绩。弘光小朝廷指着他,把长江当救命稻草,指着这道“天堑”;八旗的铁骑跺着脚骂,骂他是扎在喉咙口的鱼刺——“明末第一水寇”,不拔掉?江海永远别想睡安稳! 想想那场面吧!他麾下那帮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辽东老兵,早和海融成了一个人。驾着那种吃水浅、溜得快的沙船,在浑浊的江流里钻溜得像水鬼,浪尖上翻跟头不过是家常便饭。那船帆鼓足了劲儿,扯得咔嚓作响,布面裂开大口子,像猛兽呲出的利爪。炮管上白霜凝结,不是江南烟雨的湿冷,是火药硫磺日夜熏染的肃杀寒光。他们是崇祯年间硕果仅存的水师脊梁,偏偏活在了这个烂到根子的朝廷尾巴尖上。 整个南明王朝都压在他肩上?压吧!可那朝廷烂了芯!龙椅上的弘光忙着排场戏文,朝堂上大佬们忙着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江南膏腴之地,银子流水一样养兵,偏偏喂给黄蜚和他弟兄们的,是杯水车薪、是拖拖拉拉、是空洞的许诺!他成了孤军,一支注定被消耗、被遗忘的水上孤军。清军?看着这支飘在江上的钉子,恨得牙痒痒。黄蜚这支水军,是块难啃的硬骨头,是大清顺江而下饮马江南的巨大障碍。不啃掉他,哪能放心往南走?“此獠不死,江海不宁!”这咬牙切齿的评语,简直是给黄蜚最高的军功章!死对头的恐惧,才是一个军人最无情的赞美诗。 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沉得喘不过气。1645年那个阴冷的春天,多铎的大军破扬州,屠城十日,血浸透了运河水。史可法顶天立地的脊梁折了,弘光小朝廷在溃退中分崩离析。黄蜚还在抵抗,带着他疲惫不堪却战意未消的水师,在江海间苦苦支撑,像被遗弃的孤舟。可陆地一溃千里,水上再精的兵,也成了无根浮萍。孤悬海外,朝廷的诏书?成了风中烛火;后方的粮饷?彻底成了奢望。他成了被世界抛弃的海龙王,守着最后一点家当。 绝路。 清军的网越收越紧。一场场恶战之后,退无可退。江海茫茫,何处落脚?他那裂帆的沙船,那结霜的火炮,还能劈开这铁桶般的重围吗?结局带着必然的惨烈——据说,是哑着嗓子骂贼不肯降服后,选择了与船同沉,或者自戕明志。没有屈膝,没有求饶,只有哑声的痛斥,只有流尽的最后一滴血。舅舅黄龙的血脉,在这一刻以更壮烈的方式,在明末苍凉的天空下划上悲怆句点。老黄家的薪火,终于烧到尽头,但燃尽那一刻的刺目光芒,足以灼痛史书卷页。 我们聊这段铁血往事,除了为黄蜚这样的猛将嗟叹,总忍不住追问:一个王朝是怎么一步步把自己的长城变成孤岛的?黄蜚的悲剧,绝不只是个人命运的悲歌。南明朝廷的昏聩短视、党争内耗、资源调度失败,让多少“长城”空有拔山之力,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巨墙倾颓?黄蜚和他的辽东水师,技艺精湛,斗志昂扬,是海上的绝地战士。但他们能做什么?在失去战略后方、失去物资补给、失去统一指挥的绝望境地,再高的个人勇武、再精的战术战法,都成了被风折断的桅杆。他用生命实践了对舅父、对明朝水师最后的忠诚,像一个孤独的守墓人,守着早已腐朽棺木,直至棺木连着自己一起崩塌。 想想清军送他的那个称号吧——“明末第一水寇”,里面含着多少忌惮、又有多少佩服?站在山海关外的“渔猎”铁骑看来,这个在水网里翻江倒海的硬骨头,可不就是最难剿灭的大寇?他最终败了,连带着他操练如履平地的沙船,裂帆如爪的血性,炮甲覆霜的彪悍,一起沉入了历史的深渊。这股令人胆寒的水上力量,从此绝迹于东亚水域。黄蜚的死,几乎也宣告了大明水师最后灵魂的彻底熄灭。他是旧时代水军最后喷薄的血色焰火,短暂、灼热,旋即湮灭在滚滚洪流之中。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