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上海一男知青为了回城,抛弃了农村妻子。分别时,妻子哀求地说:“带着我吧!”男知青却头也不回的走了。没想到,留给自己的却是终身悔恨…… 李云生在湖南一个小山村,家里穷得叮当响,土墙屋子漏风,爹妈靠种田养活三个孩子。她是老大,16岁辍学,挑水种地,手掌磨出厚茧。 村里人夸她眼睛亮,笑起来暖,像山里的野花。1975年,白晓峰下乡,上海来的知青,戴黑框眼镜,气质跟村里人不一样。他教书,拿支吸墨水的钢笔,写字工整得像印刷。 村里孩子围着他学字,李云也去听,学着写自己名字,笔画歪歪扭扭。他俩认识是在一场雨后,李云帮他收田埂上的衣服,聊起了上海的电车和村里的小溪。1976年,两人结婚,村里摆了三桌酒,喜糖是白晓峰从上海带来的,甜得让人舍不得吃。 白晓峰是上海工人家庭的独子,爹在厂里做钳工,娘是纺织工。他高中毕业下乡,起初不适应,鞋底磨破也不吭声,后来学会了干农活。 他教书时严肃,写板书总推眼镜,村里人觉得他有城里人的派头。跟李云结婚后,他住进她家泥屋,晚上点油灯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 李云给他缝衣服,针脚粗糙但结实。村里人都说这对小夫妻般配,可没人想到,返城的机会会把这一切撕得粉碎。 1978年,知青返城政策下来,白晓峰拿到回上海的名额。那天早上,李云抱着刚一岁的女儿,站在村口土路上。白晓峰背着旧帆布包,里面装着几本书和衣服,脚步急促。 他没看李云,头低着,手插在口袋里。李云拽住他衣角,手指攥得发白,孩子在她怀里哭得嗓子哑。 白晓峰扯开她的手,布料撕裂的声音刺耳,他扔下一句话,说上海没她的位置,然后头也不回走了。李云跌坐在地上,泪水混着泥土,村里几个婶子过来拉她,骂白晓峰没良心。她没说话,手里攥着被扯破的布,眼睛盯着远处的路。 白晓峰的离开,像把刀子捅进李云的生活。村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城里人靠不住,有的劝李云改嫁。她摇头,说要守着家,等他回来。 她每天挑水种地,扁担压得肩膀肿,晚上点油灯缝衣服,针线慢得像在数日子。她攥着结婚证,纸边发黄,里面夹着两张喜糖纸,边角磨得发毛。 她常跟女儿讲白晓峰,讲他戴眼镜的样子,讲上海的黄浦江和电车。村里孩子爱听她讲故事,她说到上海的霓虹灯,眼睛会亮一下。 李云的身体慢慢垮了,常年劳作加上心病,咳嗽越来越重。村里赤脚医生说她肺不好,药费贵,她舍不得花钱。 1985年,她开始咳血,染红了给女儿攒的嫁妆布,那块布是她省了两年口粮换来的。她还是没改嫁,村里人劝不动,她说怕白晓峰回来找不到家。 她教女儿认字,用工分本练,字迹歪斜但认真。晚上她坐在炕上,油灯晃得影子乱动,手指摩挲着糖纸,像是怕丢了最后那点念想。 白晓峰回了上海,进厂做文职,穿上蓝色工装,抄写报表。1980年,他结婚,妻子是厂里会计,婚礼在小饭馆办,桌上摆着汽水和瓜子。 他住进筒子楼,窗外是弄堂的叫卖声。生活平淡,他没再提李云,但每年清明,他会去黄浦江边,握着支旧钢笔,盯着江水发呆。1990年,他回村打听李云,村里人说她死了,他蹲在老榕树下,眼泪滴在土里,手攥着钢笔没松开。 李云到最后也没等到白晓峰。1987年,她病逝,躺在土炕上,瘦得只剩骨头。临终前,她摸着女儿的脸,手指冰凉,糖纸从枕头下露出一角。 女儿后来考上师范,穿着李云留下的棉袄,成了村里第一个女教师。白晓峰晚年常去黄浦江边,头发花白,手里还是那支钢笔,江风吹得他衣角翻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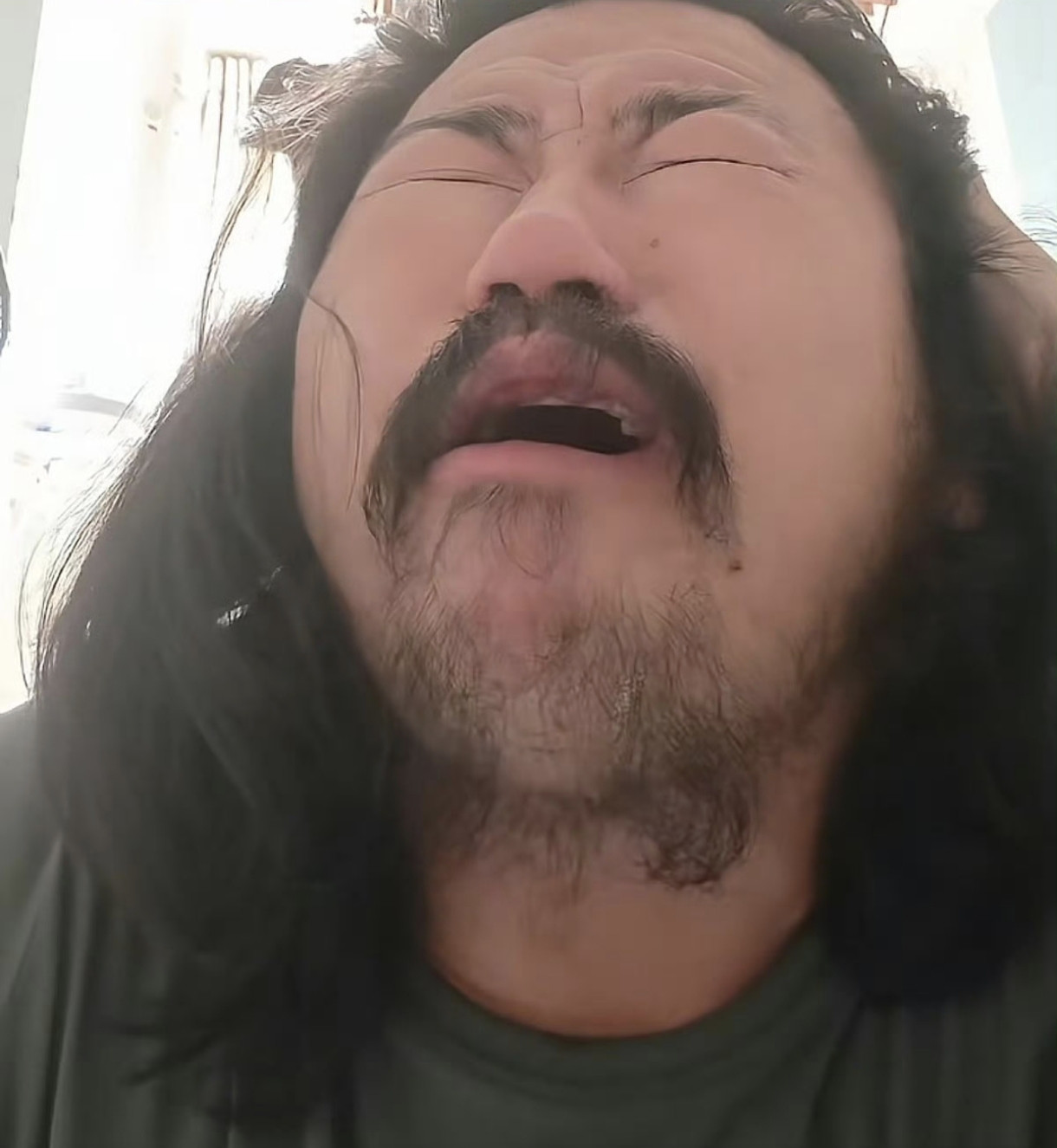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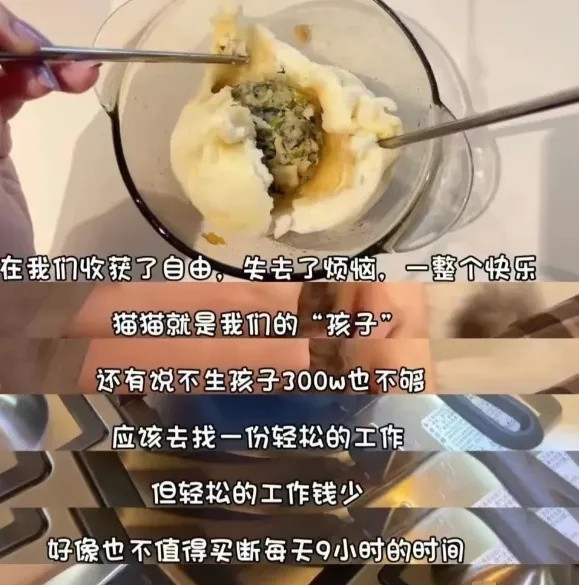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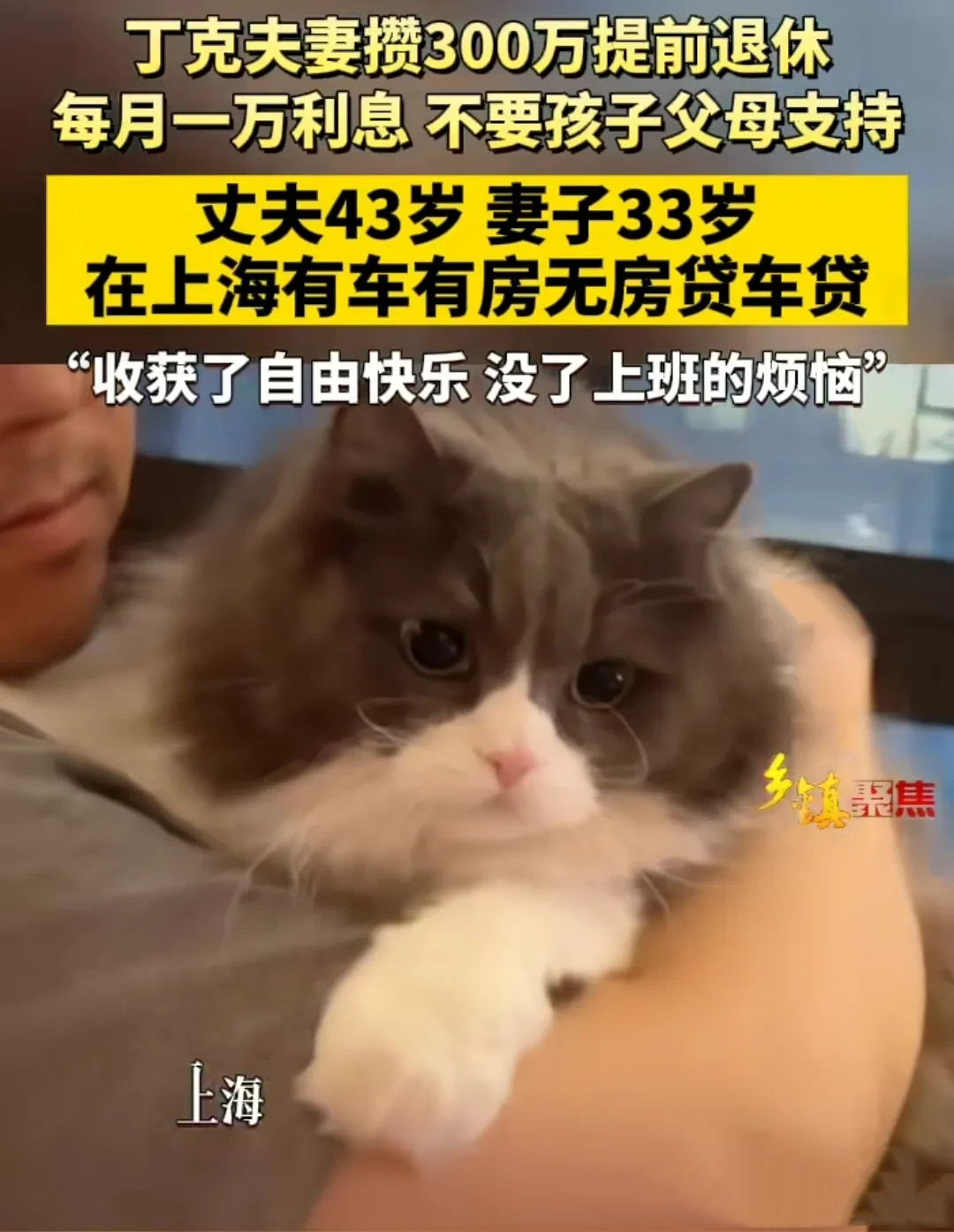


冬天不冷
不知所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