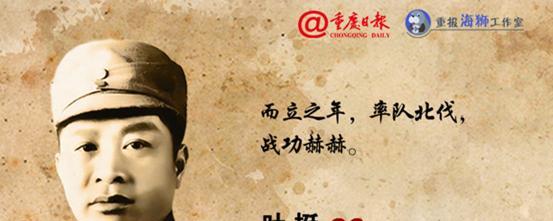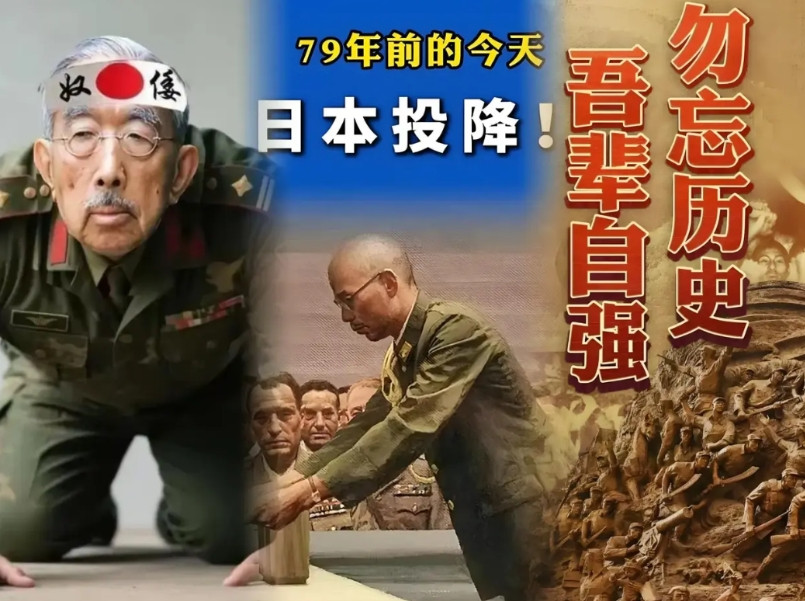1936年鲁迅病逝后,苏雪林公开撰文怒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 “1962年秋天,你说那位女教授为什么对鲁迅抱了那么深的怨气?”台湾师大图书馆的阅览室里,一名年轻助教翻着泛黄的《大公报》,忍不住低声向老同事发问。对话只持续了几秒,却恰好点出了一个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延续至今的谜团——苏雪林与鲁迅之间的爱恨反转。 从时间线往前推回二十六年:1936年10月19日凌晨5点20分,鲁迅在上海租界内的急促呼吸中停止心跳。噩耗传开,数千读者自发赶至大陆新村的灵堂,街口花圈挤得人行道只剩下一条窄缝。当时上海各报面面俱到地报道“民族魂”的陨落,原以为声声叹息会持续许久,谁料三天后,一篇四千字的檄文却像冷箭破窗——作者苏雪林。 苏雪林本名苏禹娴,安徽太湖人,留法、再赴比利时,归国后任中大、武大教授,笔下文章多以清丽典雅著称。早年她对鲁迅可说五体投地,1925年那本《绿天》首版还刻意选了鲁迅常用的宋体铅字,献辞写着“敬呈鲁先生”。然而热忱维持不过三年,转折点发生在1928年夏天的北新书局午宴。 宴会那天,苏雪林身上仍挂着暑气,一进门就看见鲁迅、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围坐。林语堂礼貌起身致意,郁达夫笑嘻嘻握手,轮到鲁迅,却只有一个淡淡的抬眼和点头。尴尬如火苗蹿上苏雪林面颊,她机械地收回手。有意思的是,旁人没觉得异样,可苏雪林回家后翻来覆去地想——鲁迅为什么给她脸色?朋友提醒,她常在《现代评论》撰稿,而鲁迅痛斥该刊“洋奴文学”。解释虽牵强,却像钉子一样扎进她的心。 翌年,北平女师大会同学潮爆发。校长杨荫榆开除学生,鲁迅连发数文声援青年;苏雪林却力挺旧师长。舆论短兵相接,两人正式撕破脸。彼时双方在报纸副刊隔空交火,鲁迅一句“麻司马又要舞文弄墨啦”,让苏雪林恨得牙痒。短短八年,从“先生与学生”到“仇雠”,裂痕愈演愈烈。 1935年冬,瞿秋白就义的消息传到上海,鲁迅的胸疾随之加重。朋友打算筹款送他赴日疗养,他摆手拒绝:“轻伤不下火线,我还写得动。”次年入秋,病势进入倒计时。杏林路的日籍医师救治无功,美国医生诊断“早该离世”,鲁迅闻言只笑:“看来我已赚了五年性命。”十月中旬,他写完悼念章太炎的文章,夜晚辗转咳血。最后一针强心剂没有奇迹,他的大衣口袋依旧揣着排字稿。 吊唁高潮之际,苏雪林的檄文横空。文章题为《质疑鲁迅纪念会书》,劈头一句:“鲁迅心理病态,人格矛盾,非为殉道者,乃为党国之大患。”她质问蔡元培为何愿出任纪念委员会主席,甚至称鲁迅“以刻毒为能事”。措辞尖刻,引发全国舆论风暴。短短十余天,各地报刊批驳文章累积可堆满半张榻榻米。苏雪林却将剪报分类装盒,还得意地称:“重五斤有余,可以当枕头。” 为何她一定要把鲁迅钉上耻辱柱?抛开私人恩怨,还有意识形态的分野。苏雪林的文化立场偏重西洋天主哲学,她对左翼“革命文学”多抱戒心;鲁迅则站在“左联”前沿,火力集中扫射旧文学与旧道德。两条轨道必然相撞。值得一提的是,胡适在这场冲突里扮演了意外角色。苏雪林致信征求意见,胡适回函提出“鲁迅之功不可抹”,劝她克制。收到信后,苏雪林竟将全文刊出,将胡适的温和批评一并曝光,从此自诩“反鲁急先锋”。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国土沦陷,苏雪林辗转香港、越南,最终逃到重庆。战火并未浇熄她的怒火,她继续写《论鲁迅的人格》等长文。抗战胜利后,她赴台湾教书,年逾花甲仍在课堂揪着鲁迅不放,口吻越发刻薄。学生问:“老师,您研究鲁迅哪部作品?”她回答:“我研究他的病态心理。”研究与谩骂的界限,从此模糊。 回到1962年台北,那位老同事放下报纸,轻声对助教说:“历史本无绝对黑白,只有时代与立场。”苏雪林和鲁迅,一个激愤地挥刀,一个冷峻地写作;他们代表的并不仅是两个人,而是民国知识界两股针锋相对的潮流。若要给这场争执下定论,恐怕谁也说不清输赢,但两把锋利的笔确实刻下了三十年代文化战场最血色的一道印痕。 鲁迅逝世八十余年,他的《呐喊》《且介亭杂文》仍在再版;苏雪林留下的《槟榔》《绿天》也依然可读。至于那篇“心理病态,人格矛盾”的檄文,如今多被收入文史选编,成为课堂讨论的反面材料。是非与功过,早已交由读者自己判断。而图书馆窗外的樟树叶哗啦啦落下,年轻助教合上旧报纸,低声感叹:“原来,两支笔能写出如此锋利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