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北京军事博物馆驻足凝望,趁四下无人时颤抖着伸出手想触碰展柜里的文物,工作人员急忙上前制止。老人眼眶泛红哽咽道:"四十年前,是老汉我背着它走完两万五千里长征路啊。" 【消息源自:《军事博物馆1976年访问记录》《江西革命人物志》1985年版】 玻璃展柜前,谢金宝的指关节在有机玻璃上叩出闷响。老人斑驳的手掌与柜内锈迹斑斑的铁疙瘩隔着四十年的光阴对峙,博物馆的射灯在那块"红军第一代手摇发电机"的铭牌上投下晃眼的光斑。 "同志,这个不能摸。"穿蓝布制服的工作人员小跑过来,胸前的毛主席像章晃得谢老眯起眼。他没理会劝阻,驼色旧军装第三颗纽扣擦着展柜边缘,发出细碎的刮擦声。 "当年在汝城,它淋了雨不发电,是我拆了绑腿布擦的线圈。"谢老江西口音混着痰音,指甲缝里还留着四十年前那场秋雨的泥腥味。1934年11月的湘南,这支由苏维埃银行金库改装的通讯队正被白军咬住尾巴,背着68公斤设备的谢金宝落在队伍最后。发电机铁壳磕在他肩胛骨上的钝痛,此刻突然在博物馆的冷气里复活。 工作人员正要叫保安,老人从内袋掏出的残疾军人证啪地摊在展台上。泛黄照片里浓眉方脸的红军战士,与眼前佝偻着背的独臂老人完成时空叠印。"您...您就是守着发电机挨了弹片的那位?"年轻人喉结滚动,展览说明牌上"长征途中牺牲十二名通讯兵护送"的铅字突然有了温度。 1932年的赣南钨矿坑道里,22岁的谢金宝第一次见到这台德国造机器。时任中华钨矿公司总经理的毛泽民拍着沾满矿粉的发电机说:"小金宝,革命不光要榔头铁镐,更要靠它传消息。"后来这铁疙瘩跟着他走过五省,在湘江血战里当过浮筒,在雪山夜宿时做过暖炉。最险是湖南汝城那夜,白军的子弹把发电机外壳凿出蜂窝,谢金宝右臂中弹仍死死箍住设备,直到增援部队赶来,卫生员从他怀里抠出机器时,发现铁壳凹槽里凝着半碗血痂。 "现在充满电的手机还没这铁疙瘩重咧。"谢老突然的笑声惊动了参观的学生队伍。有个戴红领巾的男孩钻到前排:"爷爷,这个黑箱子怎么没插头?""要插头做啥?"老人独臂做出摇柄转动的姿势,"当年我们这么摇上半小时,才够发三个字的电报——"他浑浊的眼球突然亮起来,"比如'向-北-走',就救了一个师。" 1976年的博物馆穹顶下,谢金宝的回忆像老式发报机断断续续的滴答声。工作人员默默撤走了"禁止触摸"的告示牌,人群围成的圆圈里,老人用独臂比划着当年背负设备的姿势。有个穿的确良衬衫的姑娘突然问:"您恨不恨打伤您手臂的敌人?"谢老愣了下,指着发电机外壳的弹痕:"该恨的是这些铁锈,当年白军子弹都没打穿的钢板..." 闭馆铃响起时,谢金宝最后看了眼沉睡在防弹玻璃里的"老战友"。暮色中,那坨铁疙瘩的阴影投在博物馆大理石地面上,依稀还是1934年月光下那个需要他用生命守护的"革命火种"。走出大门时,他摸出供销社退休证看了看,对搀扶他的工作人员说:"当年毛泽民同志说得对,传消息的机器,比枪炮金贵。"长安街上的车灯流成河,老人独臂的袖管在晚风里晃荡,像半面褪色的军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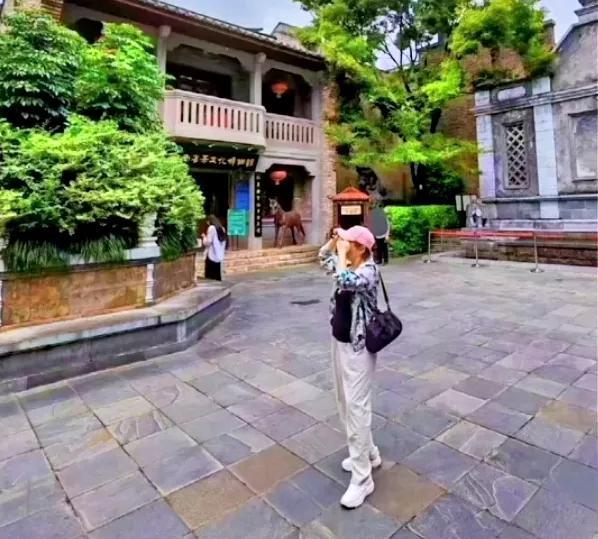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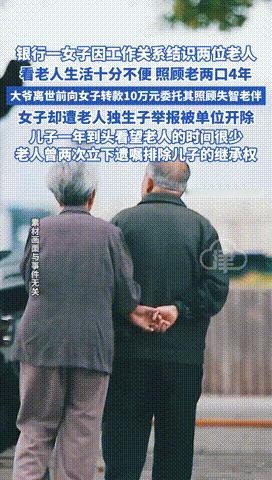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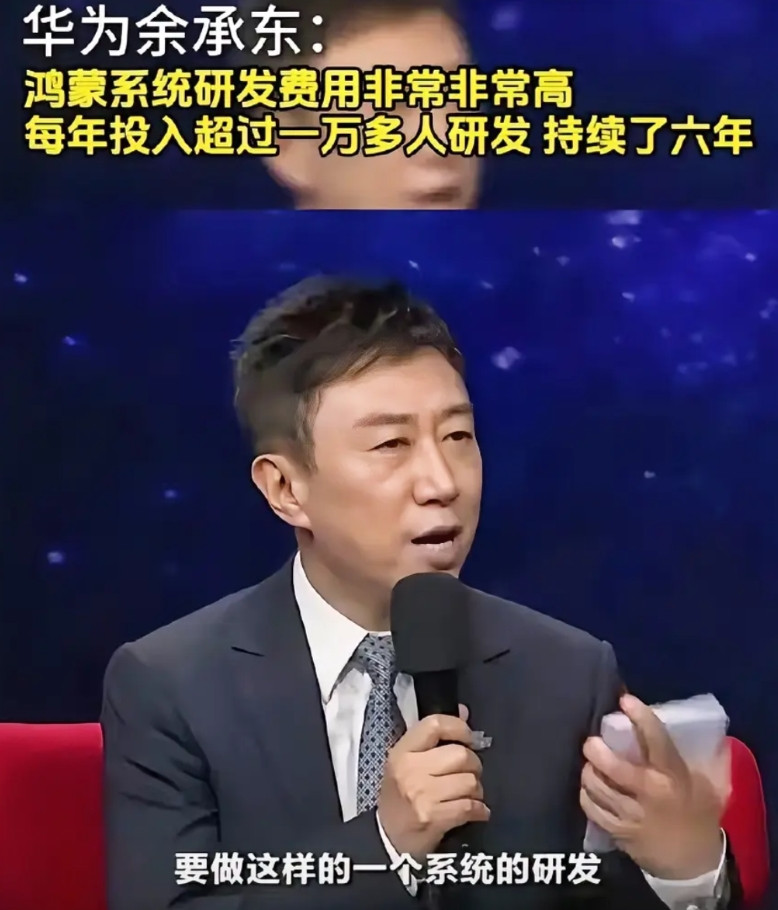

友情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致敬老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