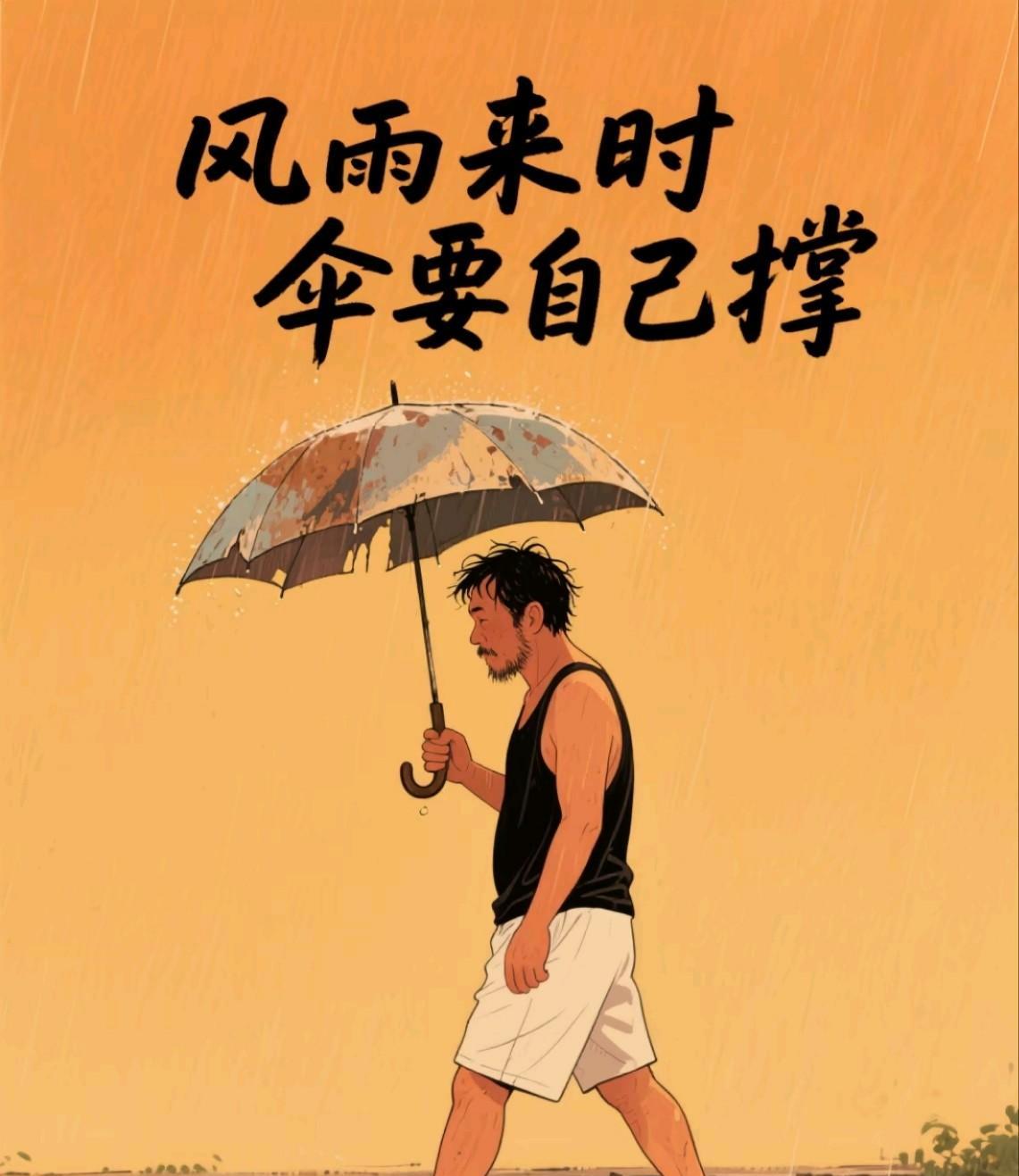1985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迎来了新一批学生。17岁的蒙古族女孩萨日娜和身高一米八二的潘军成为同班同学。三个月后,潘军因视力体检不合格面临退学,他争取到了旁听生资格,代价是没有学位证和毕业分配。
1985年上海戏剧学院表演系的练功房里,总能看到两个特别的身影。
来自内蒙古的萨日娜扎着朴素的马尾辫,正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表情控制。
角落里,旁听生潘军捧着剧本小声诵读,时不时推一下滑落的眼镜。
他们像两条平行线,直到那次分组练习。
"剩下你们两个一组。"
老师话音未落,萨日娜抬眼望向教室另一端。
那个叫潘军的男生耳根通红,手里的剧本捏出了褶皱。
排练室暖气不足,呵出的白雾模糊了两人之间的尴尬。
萨日娜主动伸出手:
"我叫萨日娜,合作愉快。"
潘军的手心全是汗。
《雷雨》选段排练到第三周,潘军突然在鲁贵独白时哽咽。
萨日娜没嘲笑他,反而递上手帕:
"这段词确实扎心。"
那天他们坐在排练室地板上聊到深夜,潘军说起童星时期的压力,萨日娜分享内蒙草原的星空。
月光透过窗户,在两个年轻人身上镀了层银边。
毕业季的宿舍楼下,潘军攥着皱巴巴的情书等了整晚。
当萨日娜抱着脸盆出现时,他脱口而出:
"老师说你是好姑娘,要我珍惜。"
话一出口就后悔了,这算什么表白?
没想到萨日娜噗嗤笑了:
"哪个老师这么有眼光?"
现实很快露出獠牙。
被分配到机修厂的萨日娜,每天要盘起长发钻进工作服。
有次下班路上,她看见商场电视里正播老同学的新剧,工装裤兜里的手攥得生疼。
潘军找到她时,她正蹲在机床边掉眼泪,油污混着泪水在脸上画出滑稽的纹路。
1990年总政话剧团分房公示那天,潘军冲进机修车间。
他单膝跪在油腻的地板上,掏出8元钱买的银戒指:
"嫁给我吧,能分11平的房。"
萨日娜手上的机油还没擦干净,戒指戴上去瞬间就蒙了层灰。
婚礼就在宿舍楼食堂办,258元的花费里,200元是早婚罚款。
转机来得突然。
1995年《牛玉琴的树》导演来选角,萨日娜正在给女儿织毛衣。
听说要下乡体验三个月,其他演员纷纷摇头。
萨日娜二话不说收拾行李,临走前把女儿托付给潘军:
"就当我又去机修厂上班了。"
在陕北窑洞的土炕上,她给家里写信:
"今天学会了赶毛驴,比修机床容易。"
首映式上,潘军抱着女儿坐在最后一排。
当银幕上的萨日娜满脸风霜地种树时,三岁的女儿突然指着屏幕喊"妈妈"。
潘军眼眶发热,银幕内外,他的两个姑娘都在茁壮成长。
金鸡奖颁奖夜,新晋影后萨日娜在感言里说:
"感谢我的丈夫,是他用11平米的房子,装下了我所有的梦想。"
台下潘军笑中带泪,怀里熟睡的女儿戴着用8元钱戒指改的项链。
如今他们的女儿已长大成人,萨日娜依然活跃在荧幕上。
每次拍完戏回家,潘军还是会像当年一样,在门口接过她的行李箱。
玄关的相框里,是张泛黄的照片:两个年轻人站在上戏门口,身后梧桐树正茂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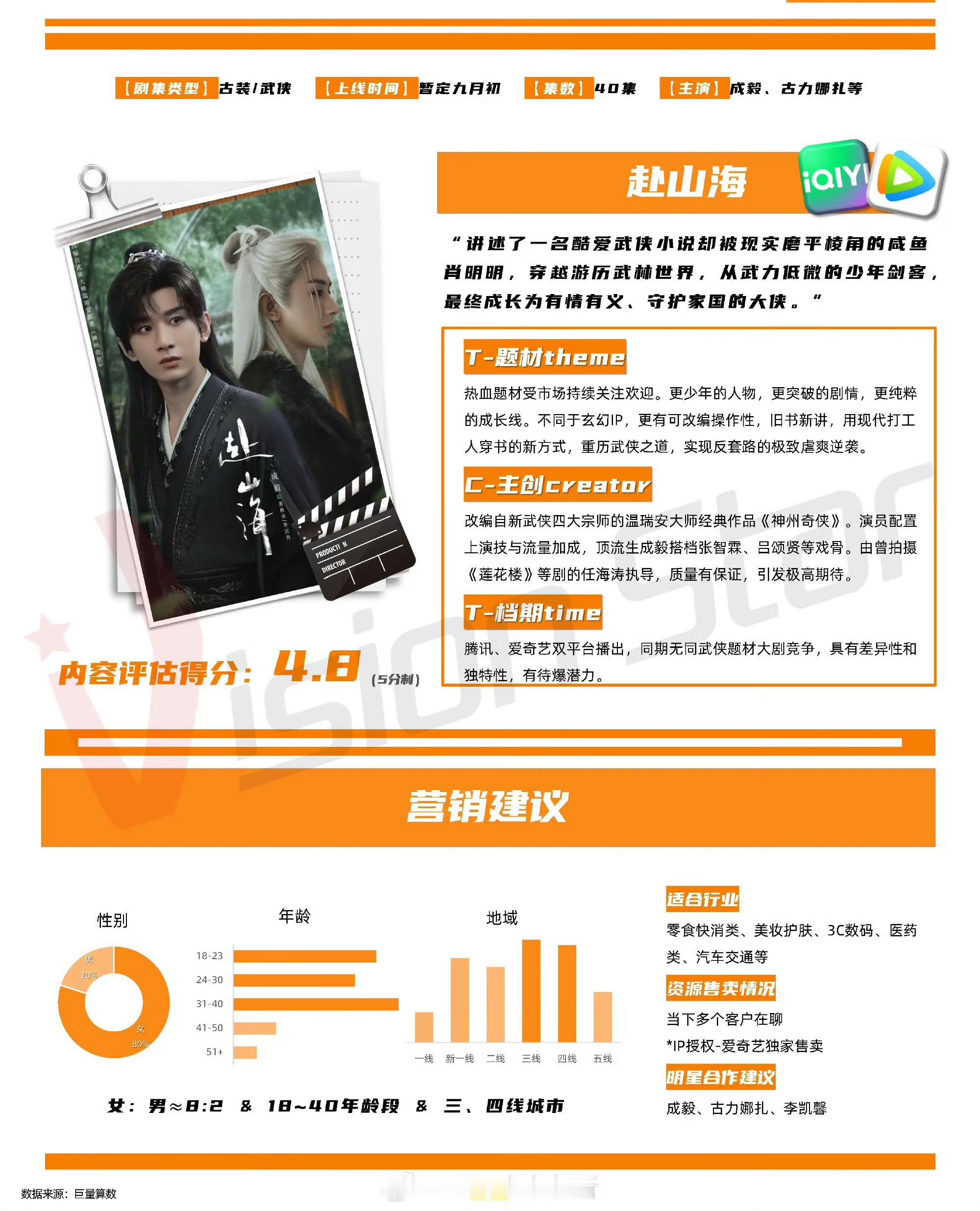


![落地德国,放眼望去看不到几辆电车[吃瓜]yz77聊车](http://image.uczzd.cn/918906862354104115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