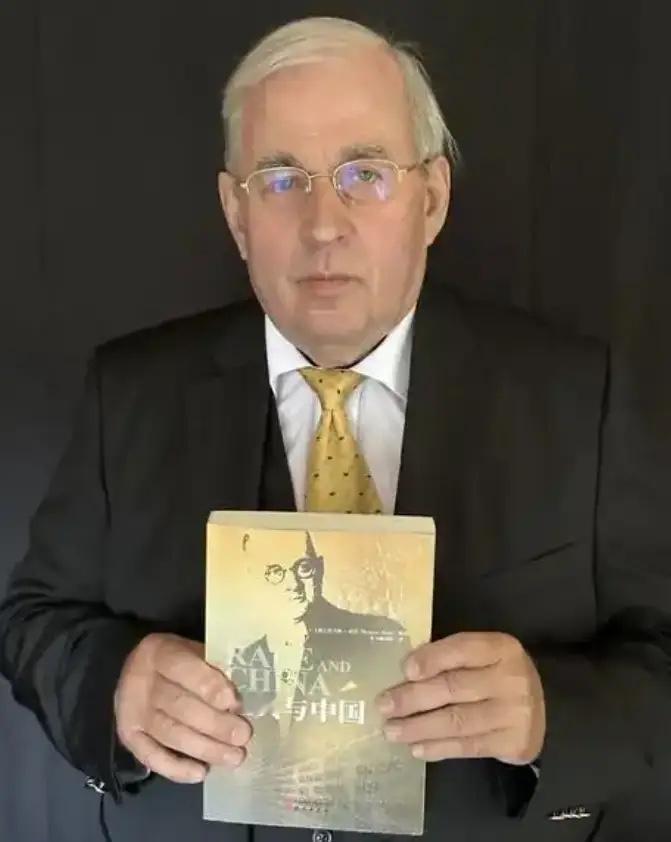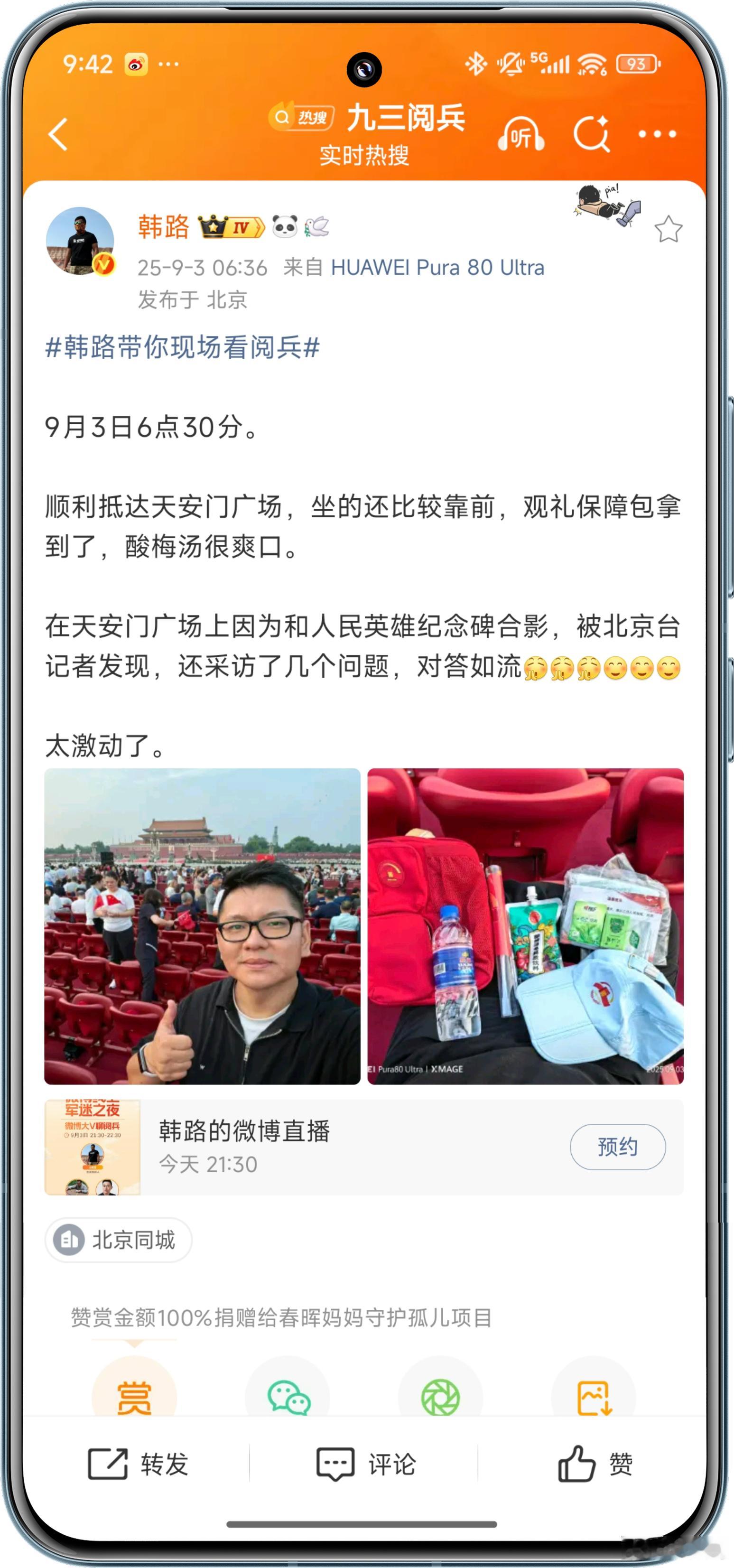1942年1月,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在参加华中局党委扩大会议时,被坐在侧边的女速记员吸引住了。这个女速记员不仅记录会议内容速度快,还长得端庄文雅。那么,这个女速记员是谁呢?后来怎么样了呢? 这事儿,还得从一场开在苏北阜宁土坯房里的高级军事会议说起。 那时候条件艰苦,屋外寒风呼啸,屋里就靠一盆炭火取暖。会上,32岁的副师长张爱萍正慷慨激昂地讲着游击战术,他可是个出了名的“儒将”,既能提笔写诗,又能上马杀敌。正讲到关键处,他眼角的余光,无意间扫到了会场角落里一个姑娘。 怪了,全场的干部都在奋笔疾书,可就这姑娘的姿势,透着一股特别。她的手腕灵活得像安了弹簧,钢笔在纸上飞舞,那“沙沙”声,节奏感十足,跟别人的完全不一样。张爱萍心里头“咯噔”一下,暗自佩服:这姑娘的手速,比我战场上给机枪换弹夹还麻利! 他忍不住多看了几眼。那姑娘低着头,神情专注,听到关键地方,笔尖会轻轻一点,然后迅速在旁边画个重点符号。别人还在手忙脚乱地补充漏掉的内容时,她已经翻过一页,开始用红笔在背面列提纲了。那份从容和专业,在炮火连天的年代,简直比军功章还耀眼。 这个让张爱萍将军“走神”的姑娘,就是李又兰。 说起李又兰,那也是一位奇女子。她1919年出生在宁波一个大户人家,父亲李善祥是位爱国实业家,在上海开纱厂,家境相当优渥。可这位“白富美”偏偏不爱红妆爱武装。1938年,19岁的她瞒着家人,一个人跑到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铁了心要参军抗日。 接待的同志看她文文静静,还带着个速记本,就考了考她。没想到,李又兰当场就展示了一手绝活,连带着浓重口音的方言土语,她都能迅速转换成速记符号,记录得一字不差。人才啊!这在当时,简直就是“最强大脑”。就凭这手硬功夫,她成了我军早期不可多得的专业速记员。 命运的奇妙就在于此。在遇到张爱萍之前,李又兰的人生已经经历过一次巨大的伤痛。她的第一任丈夫,是新四军的副军长项英。然而,皖南事变的悲剧,让她永远失去了爱人。那段日子,她把悲痛深深埋在心底,带着伤痕继续投身革命工作。 所以,当张爱萍的目光投向她时,他看到的,不只是一个手速飞快的记录员,更是一个眼神里带着故事、眉宇间透着坚毅的革命女性。 会议一连开了好几天,张爱萍的心思也跟着活络起来。他开始找各种“蹩脚”的借口往记录组那边凑。一会儿是“同志,借点墨水用用”,一会儿又是“麻烦问下,下午的会议几点开始?”。每次,他都能看到李又兰伏案工作的身影。 有天下大雪,天寒地冻。张爱萍看她冷得不停搓手,心里一疼。他把自己那双洗得发白的棉手套摘下来,快步走过去,往她桌子上一放,有点霸道又有点温柔地说:“戴上吧,手冻坏了,还怎么记录军情?” 李又兰捧着那双还带着他体温的手套,脸颊“腾”地一下就红了,半天说不出话来。 其实,她也早就注意到了这位年轻的副师长。战友们私下里都说,张将军打仗是猛将,平时却像个书生,爱读书,会写诗,甚至还会摄影。会上,他把复杂的战术编成朗朗上口的顺口溜,战士们一听就懂;会下,他路过老乡家门口,会自然地帮大娘挑满水缸。这种骨子里的文武双全和体贴入微,对任何一个女性来说,都是无法抗拒的魅力。 会议结束那天,分别在即。张爱萍鼓足勇气,把一本用油布小心包好的《论持久战》递给李又兰,说:“这书上有我做的批注,你看看,或许有用。” 李又兰接过来,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一行隽秀的小字:“愿与君共赴山河。” 这八个字,胜过千言万语。没有花前月下,没有甜言蜜语,只有一句沉甸甸的革命誓言。李又兰抬起头,撞上他明亮如星的眼睛,那一刻,她知道,自己沉寂的心,再次为一个人而跳动。 后来的故事,就像我们所期望的那样。经军长陈毅批准,1942年8月,张爱萍和李又兰在淮北根据地喜结连理。没有婚纱,没有宴席,只有同志们的真诚祝福。他们的“婚房”,就是一间简陋的土坯房;他们的“蜜月”,就是在反“扫荡”的枪炮声中度过的。 从那一刻起,他们相濡以沫,走过了61个春秋。 战争年代,李又兰背着速记本,跟着部队南征北战,记录下丈夫的每一次战斗部署,也分担着他的每一次殚精竭虑。和平建设时期,张爱萍将军投身国防科工事业,成为新中国“两弹一星”的元勋之一。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背后,都有他和夫人的心血。李又兰也一直在他身边,从一名速记员成长为国防科委的办公室副主任,是他的战友,更是他最坚实的后盾。 他们的四个子女,后来也都子承父业,投身军队和国防建设事业,个个都非常出色。比如他们的长子张翔,后来做到了第二炮兵副司令员,是中将军衔。次子张胜写了一本书叫《从战争中走来》,把父亲的传奇一生记录下来,让我们今天能读到这些珍贵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