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的杜博导凌晨三点写完第四遍基金申请,转身从实验楼跳下,留下遗书。 一个月内,高校第二次出现同因悲剧。 他想要的是保住实验室、保住学生、保住职称,于是把24小时切成碎片塞进数据、PPT、报销单。 基金命中率不到15%,他赌上睡眠、家庭、甚至命。 制度把“非升即走”写进合同,把“经费到账”当生死线,却把心理辅导放在网页角落。 那位四十岁出国刷墙、开车、考证书的副教授夫妇,用五年时间把收入翻了三倍,孩子进大学,他们说“没后悔”。 两条路摆在眼前:一条用命换指标,一条用汗水换生活。 高校如果继续只数论文、不看人,下一份遗书也许已经在打印。 人到底该为指标活,还是为日子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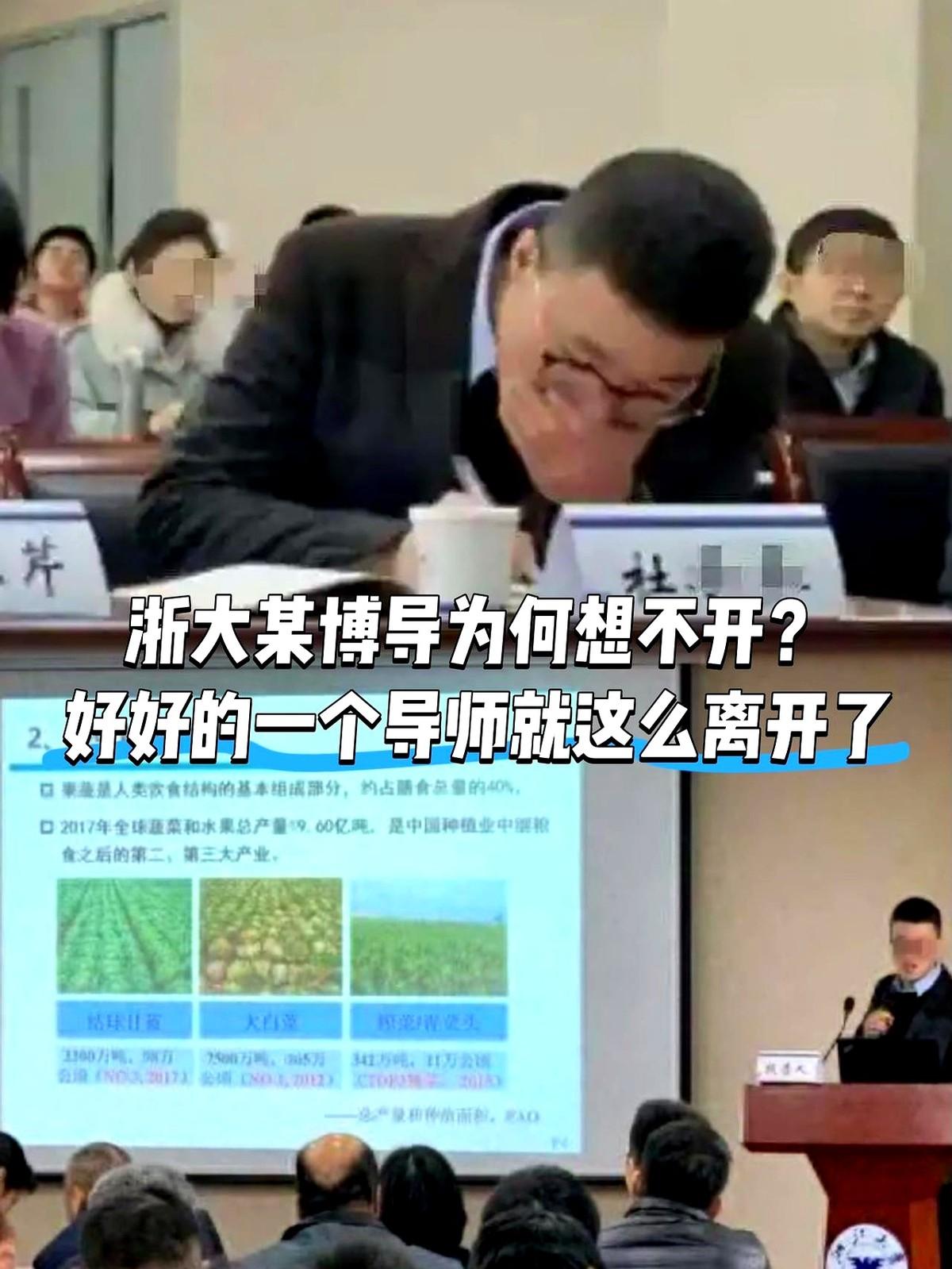

湛蓝
教育部人事部有责任
用户10xxx20
自己生活方式自己选择。
淡盐
太卷了,很多人深陷其中,深受其害
丑石
深陷其中无法挣脱,生命没有必然活着的锚点,容易放弃
用户10xxx28
大学的目标不是教书育人吗
用户82xxx76 回复 08-28 22:14
本来是,现在变成搞科研了[滑稽笑]
不负时光
没有科研能力,不要到高校混。欧美失业的博士不少,他们有自知之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