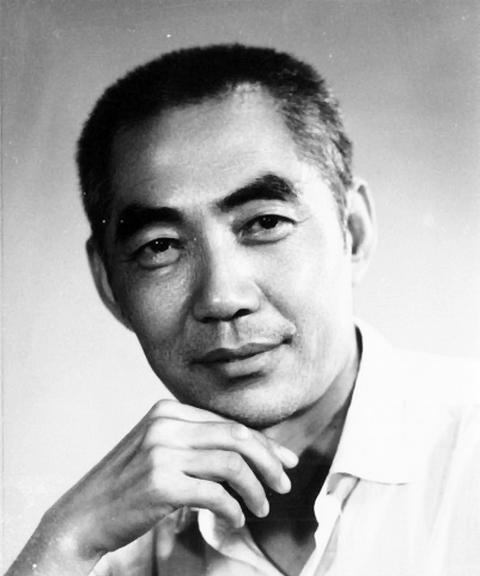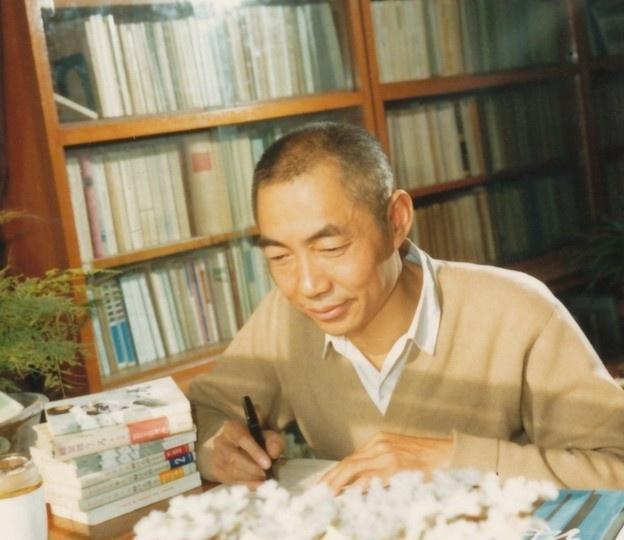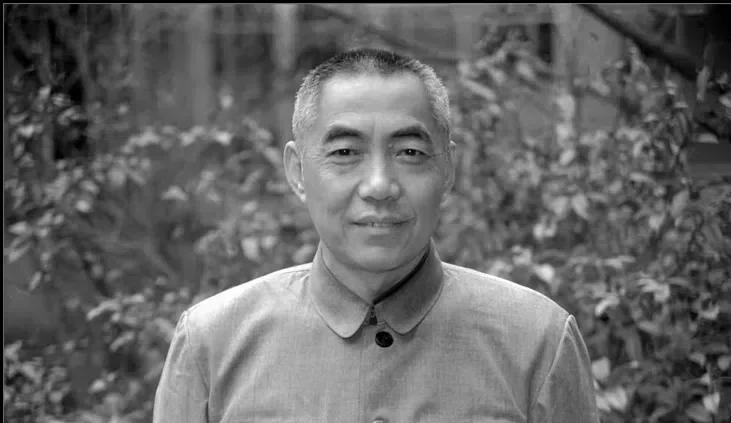1998年,在采访浩然后,胡锡进曾直言:“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浩然对乡土文学是有贡献的!”“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乐土活泉已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 2008年,浩然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洵河水涨,草木青青。浩然和夫人杨朴桥的墓地坐落在洵河东岸的冀东平原深处。浩然的塑像前,一泓泉水汩汩流淌,倾诉着他对三河大地的眷恋。墓穴右侧是按照浩然在三河居住了16年的小院原形建造的“泥土巢”;左侧是镌刻在大理石碑上的金色笔迹,那是1987年浩然亲笔书写的“我是农民的子孙,誓做他们的忠诚代言人”,这也可以看作是这位一辈子“写农民、为农民写”的人民作家的墓志铭。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他十几年不改初衷,以三河这块沃土为基地,为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军倾尽心血,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 浩然曾经谈及过自己对文学的看法,他说文学作品具有宣传和教育的功能,这可是他文学观念里相当核心的一部分。随着时间推移和认知深化,他越发坚定了这个看法。不过呢,回头想想,他发现自己以前对“宣传和教育”功能的理解,着实有点偏狭和机械了。文学作品那可是艺术品呀,只有把文学作品处理得艺术化,才能让它真正发挥“宣传和教育”的作用。从那之后,浩然在创作方法和手法上就开启了努力探索更新的征程。 早在 1962 年,浩然就写过一篇创作谈《永远歌颂》。在这篇文章里,他谈到了很多文学创作上的根本性问题。他说:“你为什么要写作?为个人兴趣呢,还是个人的名利?把它作为个人的事业呢,还是作为革命事业的一部分?你写什么?站在什么立场和角度上观察、表现生活?是歌颂,还是暴露?这些,都是一个搞文学创作人的根本性的问题,并非仅仅是写作形式和方法;它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从浩然的话里,我们能感受到他对文学创作的认真和执着,他把这些问题看得特别重,觉得这不仅仅关系到写作技巧,更关系到作家的立场和使命。 浩然还强调,“歌颂还是暴露”不仅仅是写作形式和方法的问题,更是搞文学创作“根本性的问题”,是“革命作家与非革命作家的分界线”。作为一名革命作家,党员作家,浩然做出了自己的选择,那就是“永远歌颂”。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自觉的”选择。他这么解释自己的选择: 第一,咱们是无产阶级革命队伍里的一员,奋斗目标是共产主义。以文学为武器,参加斗争,这是不可推卸的光荣职责。这就规定了,枪口只能对敌人,不能对自己。在浩然看来,文学就像一把枪,得朝着正确的方向开火,不能伤害自己的同志。 第二,共产主义事业是广大劳动人民自己的事业,符合人民的最根本利益。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目标,人民需要自己的文学,这种文学能帮他们团结、进步,给他们鼓劲。相反的,那种让他们离心离德、泄劲的文学,人民肯定不会批准。浩然把人民的需求放在首位,认为文学应该为人民的利益服务。 第三,乾坤扭转,时代大变,生活面貌焕然一新,主流是朝着人类最美好未来前进的,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这一切,为文学提供了最崇高、最丰富的创作素材。所以,文学只有歌颂这个主流,为其胜利开道,创作本身的道路和天地才是最宽广、最自由的。浩然觉得,文学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歌颂美好的事物,这样才能有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