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到底能有多苦?这么说吧,现代人吃的苦,在古人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连九牛一毛都算不上。 唐代有个叫李密的人,写了篇《陈情表》,感动了后世无数读书人,他说自己不愿做官,因为家里有个年迈的祖母靠他照顾。 他不是矫情,是因为那时候真没人能保老人吃饱穿暖,一个壮年男子不在家,家里可能连柴火都烧不起。你想想,李密的祖母都九十多岁了,放在今天有养老院、有护工、有降压药,可在唐代,老人要是动不了,吃喝拉撒全得靠亲人。李密要是去京城做官,哪怕只走半个月,祖母可能连口热粥都喝不上——那会儿没有外卖,没有社区食堂,街坊邻居自己都顾不上自己,哪有闲心管别人家的老人? 李密在文章里写“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这话里全是生存的重量。他得每天天不亮就上山砍柴,回来劈成小块堆在屋檐下,要是遇上连阴雨,柴火湿了烧不着,祖孙俩就得挨冻。祖母生病咳嗽,他得自己挎着篮子去山里找草药,没有药店能买现成的,更没有退烧药、止咳糖浆,找错了药可能还会出人命。有次他祖母想吃口软乎的米糕,他得攒半个月的碎银子去镇上买,来回要走三十多里路,回来时鞋子都磨破了洞。 这还不是最苦的,普通老百姓的日子比李密难十倍。就说唐代的农户吧,春天要扛着锄头去地里翻土,没有拖拉机,全靠人力,累得直不起腰也不敢歇,误了农时就得饿一年。夏天遇上旱灾,得挑着水桶去几里外的河边打水浇地,一天下来肩膀磨出血泡,水还不够浇半亩地。好不容易盼到秋收,刚把粮食割下来,官府的税吏就来了,粮食、布匹、甚至家里养的鸡,都得交一部分,最后剩下的粮食掺着糠麸,才能勉强过冬。 冬天更难熬,没有羽绒服,没有暖气,穷人只能穿打满补丁的粗麻衣,里面塞点干草保暖。孩子冻得手脚流脓,大人也只能用灶灰搓一搓,根本没钱看大夫。有史料里写,有的人家冬天实在冷,就一家人挤在草堆里,靠着彼此的体温取暖,早上起来发现孩子冻僵的也不是新鲜事。那会儿要是家里的壮劳力突然生病或被征去当兵,这家人基本就垮了——老人没人管,孩子没人喂,田地没人种,用不了多久就会沦为乞丐。 现代人总说“内卷”“压力大”,可再难也能点份外卖、去医院挂个号,实在不行还有低保、救助站。古人不一样,他们的苦是扎在骨子里的生存考验,没有任何“退路”。就像李密,朝廷征召是天大的荣耀,可他不敢去,不是不爱当官,是他一离开,祖母就真的活不成了。那会儿没有“社会保障”这个说法,家庭就是唯一的“安全网”,所以“孝”从来不是空洞的道德口号,是能救命的实在事。 可即便日子这么苦,古人也没丢了心气。李密守着祖母,把日子撑了下来;农户们春天接着种地,秋天接着收粮,哪怕只剩一口吃的,也会先给老人孩子;匠人哪怕饿得手发抖,也会把活计做得漂漂亮亮。他们在苦日子里守着“活着”的本分,也守着对家人的责任。 现在我们坐在暖烘烘的屋子里,吃着热饭,生病能去医院,老人有人照顾,想想古人的日子,才更明白今天的安稳有多珍贵。那些看似平淡的日常,其实都是古人盼了一辈子的“好日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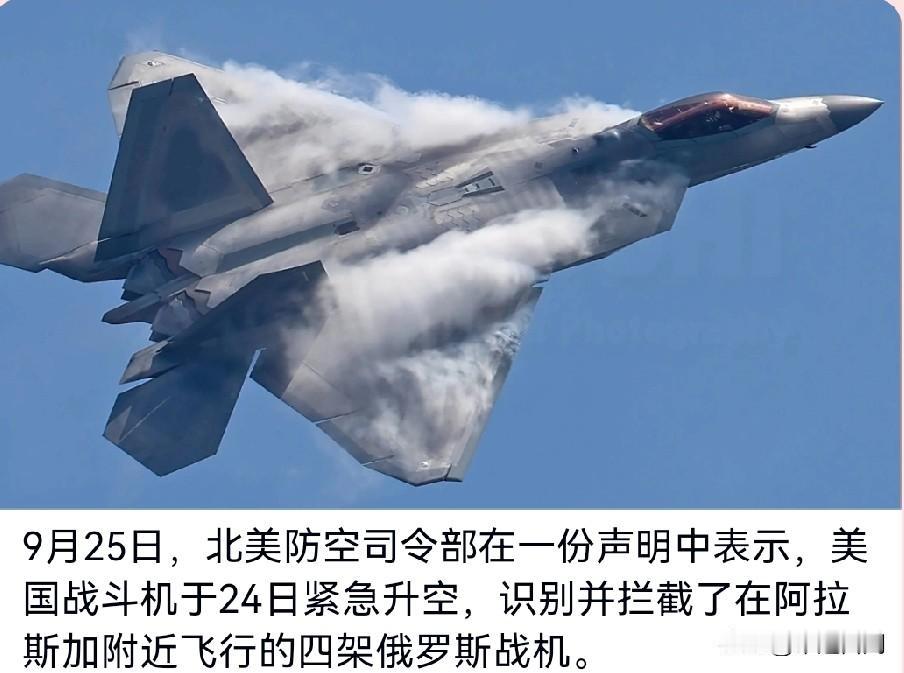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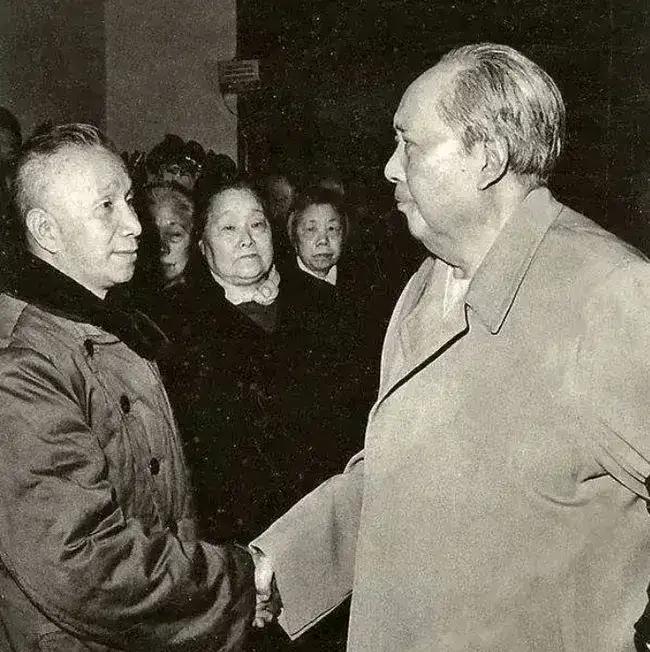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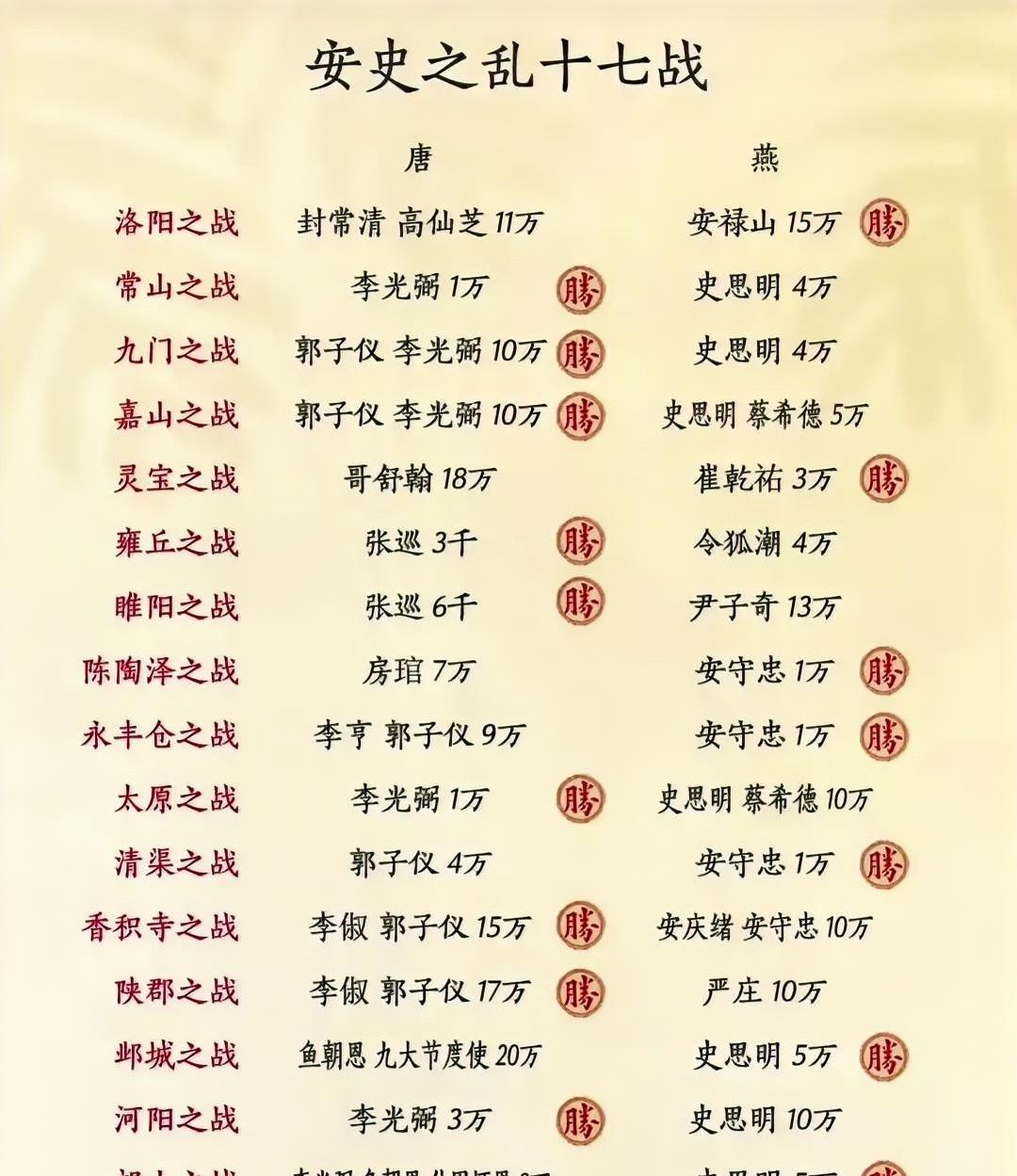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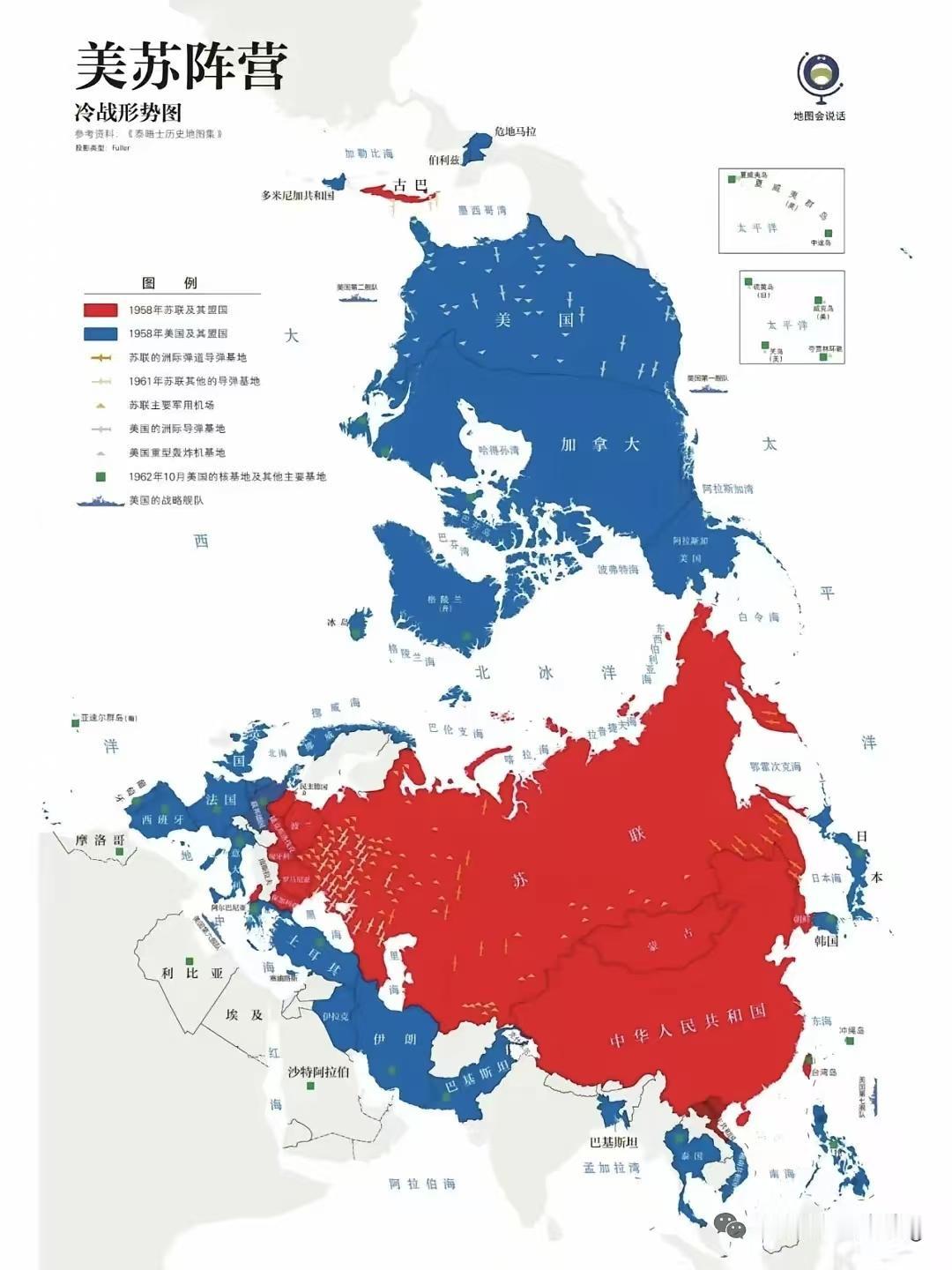


茶余饭后
四十年前也算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