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河流域的性格】马俊亚《被牺牲的局部:淮河流域的Calamity与社会重构》一书对淮河流域人的性格和行为特征进行了分析,淮河流域民众在近代以来表现出的某些负面行为特征(如一些文献中记载的“懒惰”、“狡诈”、“好勇斗狠”、“依赖性强”等),并非其固有的、天生的“劣根性”,而是长时期、高强度的灾荒和国家不公正的资源汲取政策共同作用下,被迫形成的“理性”生存策略。
1. “懒惰”与“等靠要”:生存策略的理性选择。淮河流域在近代频繁遭遇黄河夺淮、淮河自身泛滥等巨大水灾。灾后的土地盐碱化、沙化,农业产出极低且极不稳定。与此同时,国家(无论是晚清、民国还是新中国初期)的赈灾体系往往效率低下、杯水车薪。
在这种高风险、低回报的农业环境下,精耕细作式的辛勤劳动往往得不到应有回报,一场洪水就可能让所有投入化为乌有。因此,与其投入大量精力进行低效的农业生产,不如将精力用于短期内更能保障生存的活动,比如逃荒、乞讨、依赖宗族或等待政府救济。这种看似“懒惰”和“等靠要”的行为,实际上是在一个恶劣生态环境中,个体为了规避风险、保存体力而做出的最理性选择。
2. “好勇斗狠”:社会失序下的自保方式。长期的灾荒导致政府基层控制力瓦解,社会秩序崩溃,盗匪(捻军、土匪)横行。在法律和政府无法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个体和社区只能依靠暴力自保。
3. “狡黠”与“不守规则”:与“国家”博弈的手段。国家长期将淮河流域视为“牺牲的局部”。例如,为了保卫京杭大运河的漕运或保全江南富庶区,统治者会有意在淮河流域蓄洪、分洪,人为地制造灾难。同时,国家的征税和资源汲取却并未因此减少。
面对一个不公且“言而无信”的国家权力,淮河流域的民众逐渐形成了一套与基层政权周旋、博弈的行为模式。比如,虚报受灾情况以获取更多救济、隐瞒田产以逃避赋税、对政府的政令阳奉阴违等。这种在外界看来“狡黠”、“不守规则”的行为,实质上是弱势群体在强大的、不公正的国家机器面前进行消极抵抗和自我保护的“弱者武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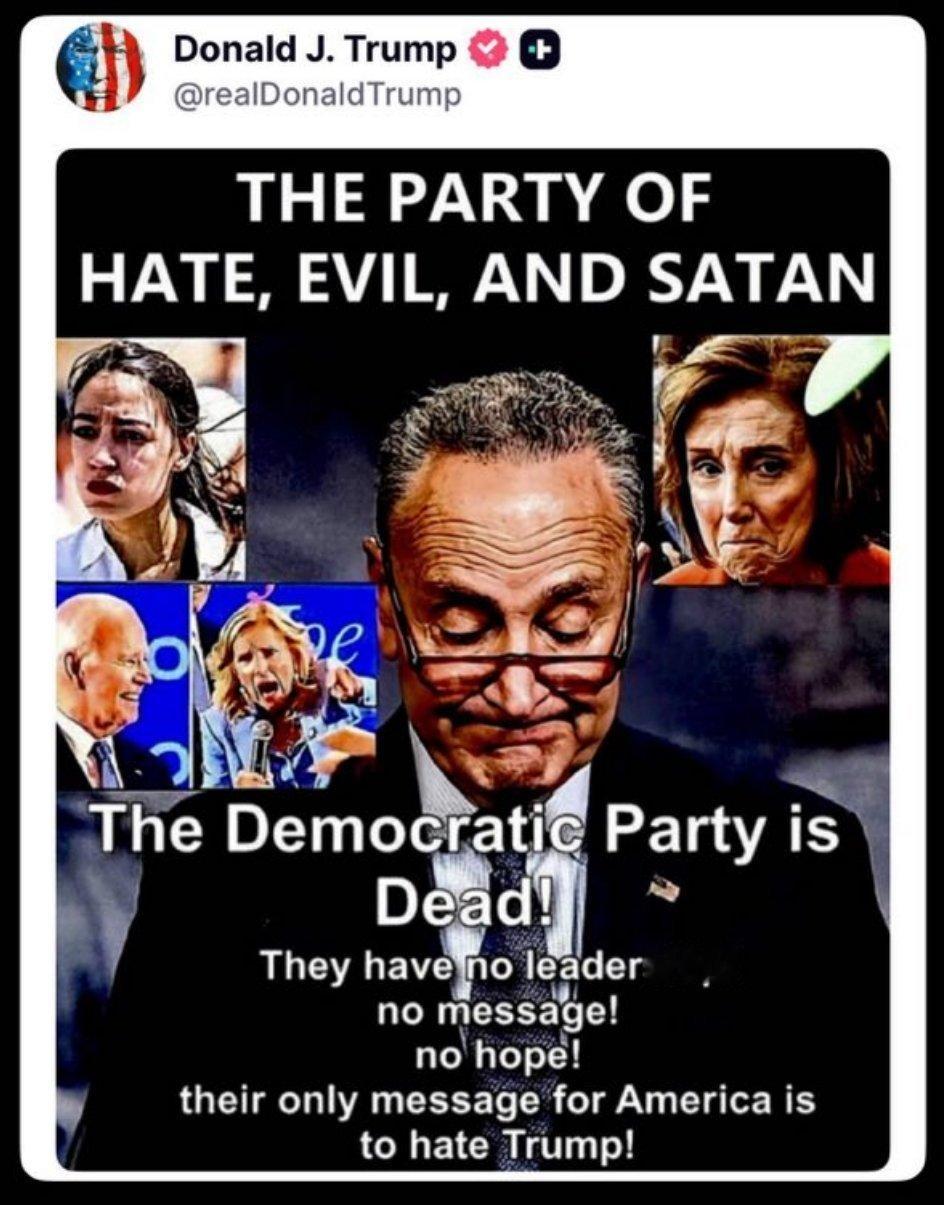


![泰山队这三中卫新星凑齐了,以后是要把赛蒂恩请来打传控吗?[捂脸哭]明天和云南玉昆](http://image.uczzd.cn/5245133296674430970.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