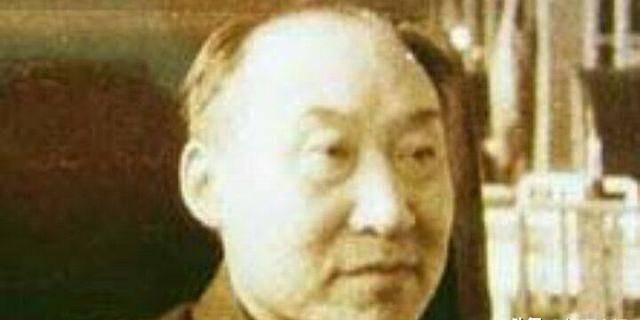1972年,钱学森在中关村大街散步时,碰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当钱学森仔细一瞧,却大惊失色,乞丐居然是自己的老师。被认出来后,乞丐却挥着手,让钱学森不要理他,离他远远的。 2024年清明,清华大学物理系的学生们捧着新印的《叶企孙年谱》,在校园西北角的铜像前驻足。铜像底座上,不知是谁放了枚褪色的黄铜校徽,校徽背面刻着“1929”。 那是钱学森考入清华的年份,也是叶企孙力排众议,把这个体检不合格却物理满分的少年,拉进科学殿堂的开始。 没人知道,这枚校徽的样式,和1972年中关村街头,叶企孙别在破衣上的那枚,一模一样。 1972年深秋的北京,粮票还是硬通货。钱学森刚结束“两弹一星”的阶段性汇报,饭后沿着中关村大街散步,想找家供销社买包茶叶。路过一家修鞋摊时,衣角突然被轻轻扯住。 他低头,先看见一只布满裂口的手:指节肿大,虎口处有道浅疤(后来才想起,那是1930年带学生做电磁实验时,被短路的电线烫伤的),指甲缝里嵌着泥,却小心翼翼捏着半块干硬的馒头。 “行行好……”声音细得像蚊子叫,可当钱学森抬眼,整个人像被冻住——那张脸虽被污垢和皱纹盖着,可眉骨间的弧度、鼻梁上残留的眼镜压痕,分明是他在清华时敬若父亲的叶企孙先生。 没等他喊出“先生”,叶企孙突然像被烫到一样往后缩,浑浊的眼睛里炸开惊恐,猛地挥手推他:“走!快躲开!别沾着我!” 那时的叶企孙,刚从监狱出来没多久。1968年冬天,70岁的他为替学生熊大缜伸冤,揣着熊大缜1938年“科学救国”的申请书,在教育部门口冻了三天。 有人劝他“别管闲事”,他却说“我是老师,不能看着学生蒙冤”。结果被按上“国民党中统特务嫌疑犯”的帽子,抄家时连他珍藏的外文期刊都被撕了,批斗会上,他被按着头跪在碎玻璃上,却始终没说一句熊大缜的坏话。 钱学森太清楚叶企孙对自己的恩。1929年他报考清华,体检时因肺功能弱被刷下来,是叶企孙拿着他的物理试卷找到校领导:“这孩子的天赋,十年难遇。” 破格录取后,叶企孙常留他在办公室补课,把自己从美国带回来的怀表拆给他看,教他“物理要动手才懂”; 1935年他要去美国留学,叶企孙连夜写了三封推荐信,还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自己攒的20美元和一本笔记:“笔记里是国内最新的研究,别跟丢了。” 在美国的十年,叶企孙定期寄学术期刊,信封上总写着“盼君早归,为国效力”。 那天偶遇后,钱学森不敢公开探望——他知道叶企孙怕连累自己。只能悄悄托清华的老校工王师傅,给叶企孙送棉衣和粮票。 王师傅后来回忆,每次送东西,叶企孙都要躲在树后看半小时,确认没人跟踪才敢拿,还总说“别告诉钱先生,别耽误他的事”。 有次王师傅看见他把棉衣里的棉絮拆出来,缝进更破的单衣里,问他为啥,他说“这棉衣太新,怕被人盯上,给孩子们惹麻烦”。 1975年,叶企孙的隔离审查终于解除,钱伟长、周培源带着奶粉去看他,发现他住在北大一间8平米的小屋里,墙上贴着手绘的清华二校门。 他记不清具体样子了,改了又画,纸上全是橡皮擦的痕迹。1977年1月13日,北京零下15度,叶企孙躺在病床上,手抓着床单反复念叨“回清华”,直到呼吸停止,那顶莫须有的罪名还没摘掉。 他的葬礼只有七位老学生敢来,有人偷偷带了朵白菊,放在他常穿的旧中山装口袋里。 他的骨灰在八宝山存了37年,直到2013年,127名海内外学者联名呼吁,才终于送回上海福寿园。 同年,清华园里立起他的铜像,铜像手里拿着一本翻开的书,书页上刻着他当年对学生说的话:“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现在每天都有学生在铜像前放笔记本,有人写“叶先生,今天物理考了95分”,有人画小小的校徽贴在底座上。 2024年,清华大学物理系开了门《叶企孙与中国近代科学》的选修课,第一节课上,老师播放了一段修复的录音。 那是1952年叶企孙在清华的讲课声,温和却有力:“你们要记住,读书不是为了自己,是为了让国家站起来。”教室里的学生们低着头,笔记本上写满了这句话。 上海福寿园的墓碑前,常年放着清华的校徽和物理课本,每到清明,总有老人来献花,其中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总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手里攥着一本旧笔记,笔记扉页上,是叶企孙当年的签名。 现在,叶企孙的名字早已被写入清华校史,《叶企孙文存》再版了五次,他培养的学生,早已撑起中国科学界的半壁江山。 清华铜像前的校徽换了又换,可每一枚,都刻着他当年教给学生的道理:风骨,比名利更重要;家国,比生命更重。 信源:有一次,钱学森在中关村大街散步,遇到一个乞丐向他乞讨_迅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