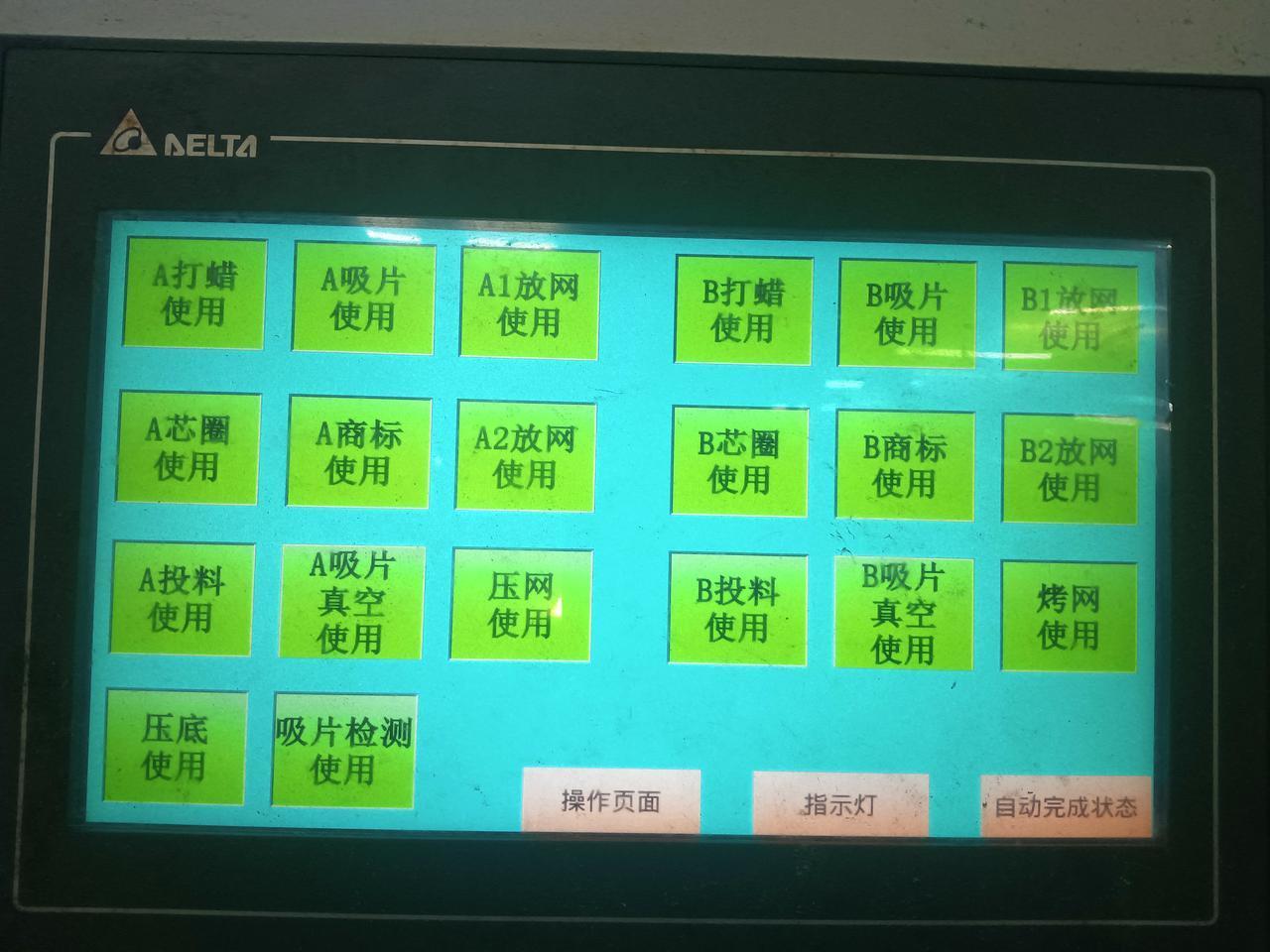我这辈子见过最震撼的场面,不是什么名山大川。 是在凉山,我朋友老家,一辆皮卡倒车进院,满当当一车斗的啤酒。 我问这是干啥,朋友轻描淡写:过年啊。 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不是来做客的,我是来渡劫的。 你以为过年是吃饭?错了,那是按顿清算你的“社交价值”。 早上八点,眼睛还没睁利索,大哥端着酒就进来了,说“喝一个,清醒一下”。 我当时就懵了,这哪是清醒,这是直接往我天灵盖上浇乙醇啊。 上了桌,没有杯子,全是箱子。 人家的热情,不是“我敬你一杯”,而是“兄弟,这箱是你的”。 那句“喜欢你才灌你”,我算是彻底体会了。 我感觉我的肝,在那两天里,提前体验了火葬场的高温服务。 我不是在喝酒,我是在输液,只不过输的都是工业酒精。 我后来琢磨明白了。 那不是酒,那是他们滚烫的情义和粗粝的生命力。 你喝的不是液体,是他们一年到头的喜怒哀乐,是把你当自己人的“投名状”。 所以别问我彝族年好不好玩。 我只能说,那是一场拿命换交情的局。 你得带着敬畏去,带着一个钢铁铸成的肝去。 不然,真的,竖着进去,能不能竖着出来,全看老天爷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