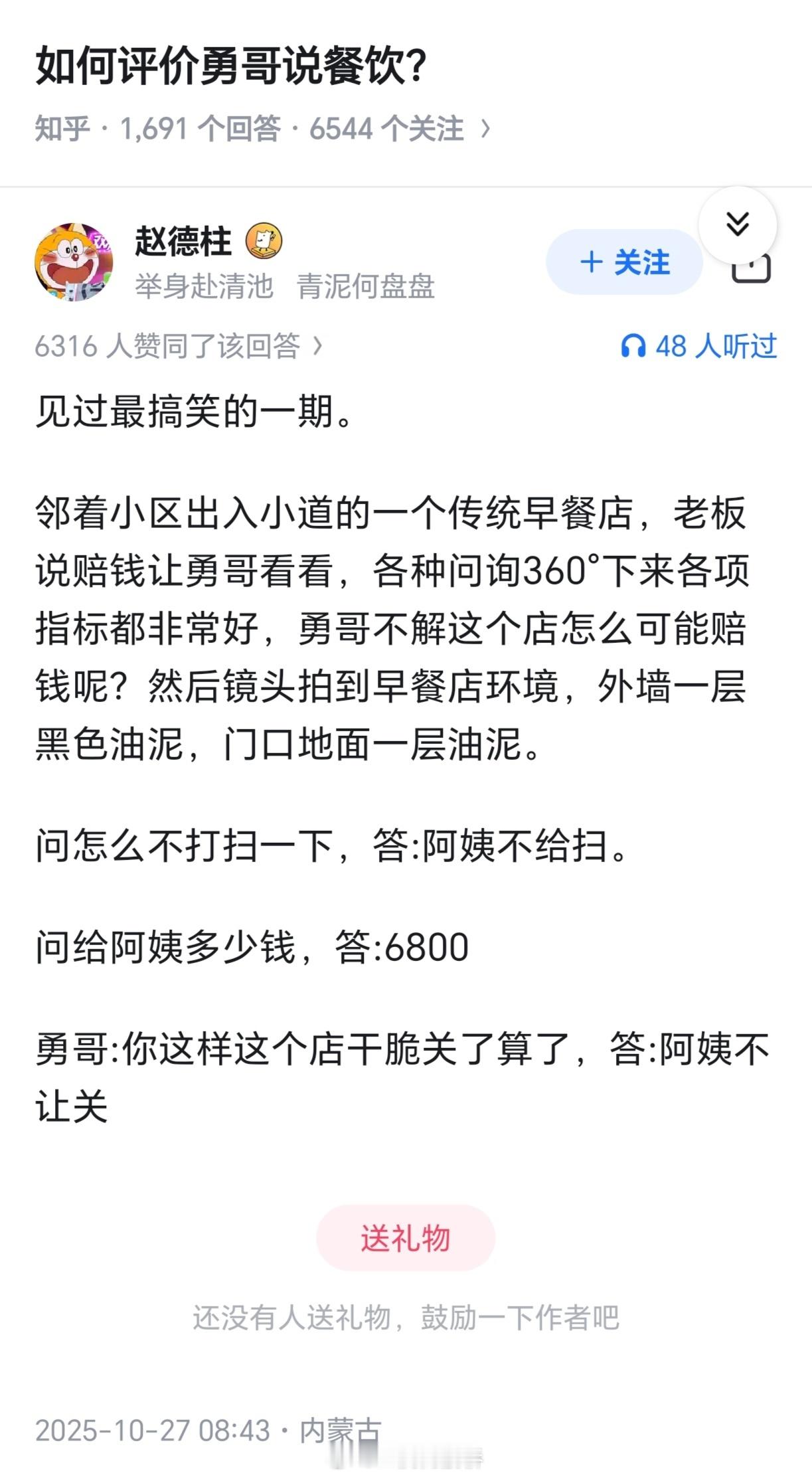王大爷今年七十二,住的是市中心老家属院的一楼,带个小院子。这房子是他年轻时在国营工厂上班分的,后来房改买断,房产证上写的是他自己的名字。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是老伴还在的时候栽的,现在每年夏天还能结满红彤彤的果子。王大爷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拎着水壶给石榴树浇水,再把院子里的石板路扫一遍。然后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跟路过的老街坊打招呼。 王大爷今年七十二,住市中心老家属院一楼,带个小院子。 房子是年轻时国营工厂分的,后来房改买断,房产证上就他一个人的名字。 院子里那棵石榴树,是老伴还在的时候栽的,树干上有道歪歪扭扭的刻痕——三十年前她怀着小儿子,够不着摘石榴摔了一跤,气呼呼拿指甲划下的“王老头坏蛋”。 每天早上五点半,天刚蒙蒙亮,王大爷就醒了。 他摸索着穿上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拎起门后那个掉了漆的铁皮水壶,壶把上缠着圈旧布条,是老伴生前怕他烫手缠的。 先给石榴树浇水,水顺着树根渗下去,惊起几只躲在草丛里的麻雀,扑棱棱飞到房檐上。 然后拿竹扫帚扫院子里的石板路,叶子、花瓣、偶尔还有隔壁李奶奶家猫掉的毛,都扫到墙角那个铁皮簸箕里。 扫完了,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眯着眼看太阳慢慢爬过对面的楼顶。 街坊们陆续出门,张婶去买菜,路过时总会喊一嗓子:“王大爷,今儿天凉,加件衣裳!” 他摆摆手,声音有点哑:“不冷,干活热乎。” 有人说他守着老房子是念旧,其实院子里的每块砖、树上的每个疤,都是他和老伴过日子的记号;不是走不出去,是舍不得把日子走散了。 去年夏天石榴结得多,枝桠都压弯了,他踩着板凳摘了满满一筐,挨家挨户给街坊送,送到三楼赵大夫家时,赵大夫非要塞给他两盒降压药,说:“您老别总想着别人,也顾顾自个儿。” 他嘿嘿笑,说:“石榴甜,吃了心里舒坦。” 街坊们常问他,守着老房子不闷吗? 他总是指院里的石榴树:“你看这树,春天发芽,夏天开花,秋天结果,冬天落叶,一年年不重样,哪有空闷?” 其实他知道,自己不是不闷,是怕闷——老伴走的头两年,他连院子都懒得进,石榴树旱得叶子卷了边,还是张婶看不下去来浇的水。 后来有天夜里睡不着,他摸黑走到院子里,摸着树干上那道“王老头坏蛋”,突然想起她摘石榴时踮着脚的样子,想起她把石榴籽剥在白瓷碗里,非让他先尝一颗的样子,眼泪就下来了。 从那以后,他每天给树浇水、扫叶子,就像她还在时一样。 水壶底磕出个小豁口,漏水,他找块橡皮塞住,照样用;竹扫帚掉了几根竹枝,他拿绳子捆捆,还能用。 这些旧物件陪着他,就像日子还没走散。 今年春天,石榴树新抽了不少嫩枝,绿油油的,看着就有精神。 王大爷浇水时特意多往那边浇了点,嘴里念叨:“多喝点,秋天给孩子们结甜石榴。” 孩子们是街坊家的,一到夏天就爱扒着他院门口看石榴,叽叽喳喳问什么时候能吃。 他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口,看着孩子们笑,跟路过的老街坊打招呼,太阳晒得人暖洋洋的。 院子里的石板路被扫得干干净净,石榴树在风里摇着叶子,好像有个人在说:“王老头,你看,日子这不挺好的?”
王大爷今年七十二,住的是市中心老家属院的一楼,带个小院子。这房子是他年轻时在国营
白卉孔雀
2025-11-27 15:47:46
0
阅读: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