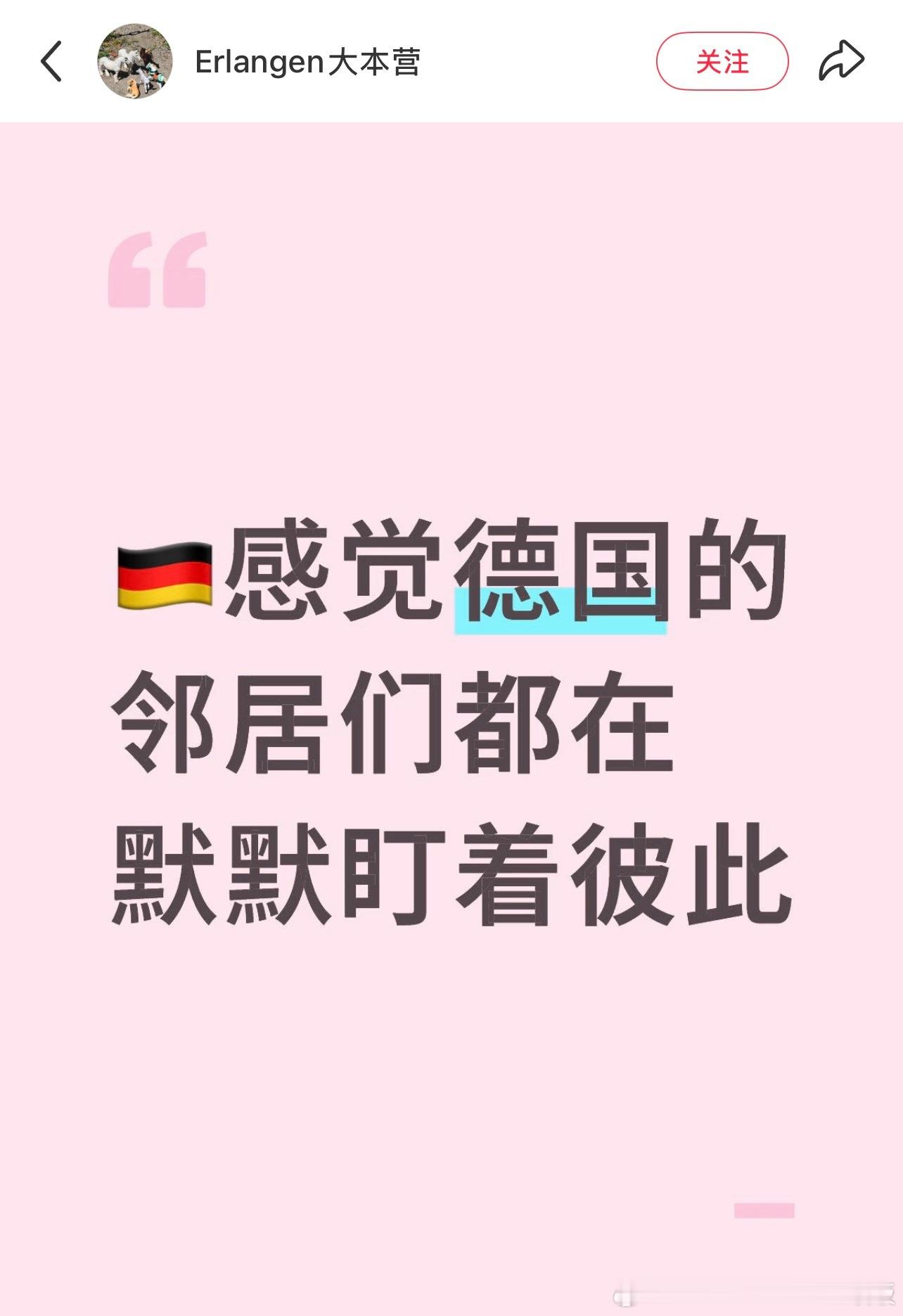几十年前,我们单位一个特务连复员在厂里任司务长,一个炊事员仗着人高马大不服,经常找事。司务长姓王,看着斯斯文文,皮肤是常年在户外练出来的深褐色,手上老茧比炊事员的还厚。炊事员叫刘勇,快一米九的个子,胳膊比一般人的腿粗,之前在工地干过,后来托关系进了厂食堂,总觉得司务长看着 “软”,好拿捏。第一次找事是在月底盘点的时候。刘勇拿着账本翻了两页, 几十年前的厂子食堂,人多眼杂,谁都想找个稳当差事。 司务长姓王,刚从特务连复员,皮肤晒得像老树皮,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看着比车间里的技术员还斯文。 可他右手虎口有块硬币大的茧子,摸上去跟砂纸似的,是常年握枪磨出来的——这是后来刘勇才注意到的细节。 炊事员刘勇,快一米九的个头,站在灶台前像堵墙,胳膊比仓库管理员老李的小腿还粗,以前在工地扛过大梁,后来托他表哥进来的,总觉得自己这身板在食堂屈才。 他瞅着王司务长不顺眼,觉得这人斯斯文文的,不像能镇住场子的样——厂里谁不知道,食堂的事最杂,采购、记账、分料,哪样不得有点“手段”? 第一次找茬,是月底盘点那天。 仓库里堆着半人高的面粉袋,空气里飘着股生虫的麦麸味,刘勇把账本往水泥地上一摔,指着其中一页喊:“王头,你这账不对啊,上礼拜领的五十斤白菜,我咋记得只用了三十斤?剩下的呢?” 王师傅当时正蹲在地上清点油罐,闻言慢慢站起来,膝盖咔吧响了一声——他关节炎犯了,阴雨天总这样。 他没去捡账本,就那么看着刘勇,眼神平得像食堂后墙那面旧镜子:“仓库门口有领用登记本,你每天签字领的菜,我都记着;后厨垃圾桶每天倒多少菜叶子,老李也帮我数着——要不,咱现在把这礼拜的泔水桶底清出来,数数白菜帮?” 刘勇愣了,他以为司务长会脸红脖子粗地辩解,或者干脆认怂说记错了,没想到这人不慌不忙,把来龙去脉都摆得清清楚楚。 那天最后是刘勇自己把账本捡起来的,手指碰到封面时,看见王师傅蹲回地上继续擦油罐,后脖颈晒脱皮的地方,新肉嫩得发红——那是前几天去郊区拉煤,顶着头晒了一下午留下的印子。 往后刘勇没断了找茬,今天说煤块太湿不好烧,明天嫌土豆个头小,王师傅都应着,煤湿了就提前一天摊开晾,土豆小了就多挑拣几遍,切菜时格外仔细,倒也没让他抓到实在把柄。 真正让刘勇闭了嘴的,是那年冬天的雪夜。 食堂后墙的排水管冻裂了,冰水顺着墙根往仓库渗,里面堆着刚到的大米和面粉。 那天值夜班的是刘勇,他拿铁锹铲雪堵水,可雪刚堆上就化,急得满头汗,棉袄领子全湿透了。 后半夜王师傅来了,不知从哪摸出根粗麻绳,在排水管裂口子的地方缠了三圈,又找了块旧轮胎皮裹上,拿铁丝勒紧,动作快得像在摆弄什么熟稔的家伙什——后来刘勇才知道,那是部队里处理装备破损的应急法子。 等把水止住,王师傅的手套早冻硬了,他摘下来哈气,刘勇才看清他手上的冻疮,肿得像发面馒头,可刚才缠铁丝的时候,手一点没抖。 “你咋来了?”刘勇递过去一个热馒头,自己先咬了一大口,烫得直咧嘴。 “听门卫老张说后墙漏水,”王师傅掰了小块馒头放进嘴里,慢慢嚼着,“仓库的米要是潮了,下个月全厂几百号人吃啥?” 刘勇没接话,就看着王师傅手上的冻疮,突然想起刚进厂时,他表哥跟他说的:“食堂这地方,别惹司务长,王头是特务连出来的,当年在边境线上,一个人追着三个特务跑了二里地。” 那天之后,刘勇再没找过事。 有次新来的小炊事员问他:“勇哥,你以前老跟王头对着干,现在咋跟亲兄弟似的?” 刘勇正切着萝卜,菜刀在案板上笃笃响:“你看王头手上那老茧没?那不是握笔杆子磨的,是真刀真枪练出来的——有些人看着软,不是没脾气,是懒得跟你计较;等他真要计较了,你连后悔的功夫都没有。” 后来仓库换了新账本,王师傅在第一页写日期的时候,刘勇凑过去看,见他手腕上有道浅疤,像条细蚯蚓。 “这疤哪来的?”刘勇问。 王师傅笔尖顿了顿,墨水在纸上洇出个小点儿:“以前训练,爬铁丝网划的。” 刘勇哦了一声,低头继续切菜,心里却透亮了——有些人的沉稳,不是天生的,是经了事,见过风浪,才把一身棱角藏在了老茧和疤痕底下。 那之后食堂仓库的账本,刘勇偶尔也帮着记两笔,他的字歪歪扭扭,王师傅的字方方正正,并排写在纸上,倒也不显得别扭。 有时候王师傅关节炎犯了,蹲不下去清点物资,刘勇就主动说:“我来,你坐着歇会儿,反正你记的账比算盘还准,我数多少你都信得过。” 王师傅就笑笑,从兜里摸出个薄荷糖递过去,糖纸在阳光下闪着光,刘勇接过来剥开,塞进嘴里,凉丝丝的甜味从舌尖一直窜到心里——他终于明白,真正能镇住人的,从来不是嗓门大或块头壮,是做事敞亮,做人踏实,像王师傅手上那层老茧,看着粗糙,却能稳稳托住该担的责任
我老公的一个发小,年轻时长的高大帅气,追他的小姑娘一大堆,后来和一个父母都是国家
【38评论】【17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