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风]粟裕要守住黄桥,一个支队长突然问道:“我算过了,我们的弹药根本守不住黄桥!”粟裕放下茶杯,笑了笑,说道:“你算的很对,我们的弹药的确不够,我们要靠地形,诱敌深入,短距离突击。” 一九四零年九月,苏北指挥部的会议桌上,茶水早都没了热气,除了满屋子的烟味,压在每个人心头的是一道几乎无解的算术题。 有人伸出指头在桌沿上不停地敲着,那是算数时的习惯,这一仗怎么算都是输:新四军这点家底,满打满算七千人,除去后勤机关,能摸枪的刚过五千,而对手韩德勤压过来的是整整三万大军,二十几个团的兵力。 “按照防守打,这仗没法接。”三大队那边的指挥员算了整整三遍,手里那点步枪子弹,人均二十发,就算不吃不喝硬顶,四个小时后黄桥就是一座空城。 这还没算对面火力上的绝对碾压——哪怕是撇开人数不谈,韩德勤手里的独立六旅,那是号称“梅兰芳式部队”的嫡系,全套德国和捷克造,光鲜得像是来唱戏的,可谁都知道那全是能吃人的钢盔和机枪。 这种“叫花子与龙王比宝”的仗,按常理得找软柿子捏,但站在地图前的粟裕,盯着那纵横交错的水网,手里那根烟转了半天也没点上,他突然给出了一个让全屋人头皮发麻的解法:不要挡在外面打,要放进来打,而且,必须先打最硬的那个——翁达的独立六旅。 这不是简单的军事战争,而是一场基于心理和地形的精密计算。 粟裕看准了黄桥周围独特的地理结构:这地方被河道切得稀碎,那是典型的“豆腐块”地形,翁达这人傲气,他是韩德勤的心头肉,也是正经军校出身,但这恰恰是死穴。 这种正规军讲究排场,带着汽车、骡马和重炮,队伍拉得有七八里长,一旦挤进黄桥北面那条只能容纳一辆车通行的狭窄土路,那就是一条被塞进管子里的蛇,再厉害的“七寸”也动弹不得。 为了把这条蛇诱进来,战场上出现了一幕极其违反军事常识的部署,黄桥外围挖了三道战壕,但这兵力配置却是个倒三角:最外头放十个班,中间五个班,到了离镇子最近的一百米处,只留两个班。 这种层层“减灶”的打法,就是演给骄傲的翁达看的。 十月四日正午,日头最毒的时候,独立六旅果然大摇大摆地到了,翁达骑在大马上,看着前头稀稀拉拉几声枪响人就跑的“抵抗”,嘴角大概是带着笑的。 在他的视角里,这就是一群不堪一击的游击队,前面的部队已经涌进了黄桥镇口,后面的重武器还在几里外的桥头上慢吞吞地挪动,他根本不知道,就在这看似空虚的黄桥镇背后,几十个烧饼炉正日夜不熄地烤着干粮,担架队早就候着,甚至连此时寂静的屋顶上,都趴满了抱着手榴弹的民兵。 当队伍完全挤进那个致命的一百米距离时,三颗红信号弹打破了平静。 刚才还安静如水的村镇瞬间炸开了锅,这就不是那种拉开架势的阵地战,而是贴身肉搏。狭窄的地形让翁达那令人羡慕的行军纵队瞬间成了活靶子,所有的重机枪和山炮根本没有展开的角度,反倒堵死了步兵撤退的路,民兵从房顶上往下砸手榴弹,主力部队则像是早就憋足劲的猛虎,直接将长蛇阵截成了三段。 这位不管是装备还是学历都高人一等的旅长彻底被打蒙了,这根本不是他教科书上学过的仗。前面找不到主力,后面又全是炸点,那些崭新的捷克式机枪直到变成了废铁也没打出几梭子。短短三个小时,这支韩德勤手里的王牌就像掉进绞肉机的碎肉,没了人形。 这时候再看所谓的“兵力悬殊”,就是个笑话,粟裕这着险棋一落地,局势瞬间翻转。因为先打掉的是韩德勤最倚重的嫡系,旁边那两个原本就心怀鬼胎、听调不听宣的杂牌旅一看翁达都完了,哪还有心思拼命? 当那个算数的大队长满脸黑灰,提着缴获的机枪冲进指挥部大喊“发财了”的时候,粟裕只是看着窗外重新泡了一壶茶。 而在黄桥镇外的一座破旧土地庙里,曾经不可一世的翁达,在绝望中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他不愿承认自己败给了一群“泥腿子”,留给卫兵的话还是要面子的“没给中央军丢人”。 与之相比,那个原本想来捡便宜的第八十九军军长李守维就更狼狈了,大部队一哄而散,这位中将在逃跑时脚下一滑,掉进了八尺深的沟里,活活淹死。 这场仗打完,谁都看明白了,原来的弹药是按防守算,二十发那是等死;但要是换了战法,利用骄兵必败的人心和这纵横的水网,那就是另一笔账了,河水东流带走了三万大军的虚张声势,留下的只有一个铁一般的事实:最好的算计,从来算的不仅仅是枪炮,更是地形与人心。 参考:解密:粟裕在黄桥战役中做的三道“数学题”人民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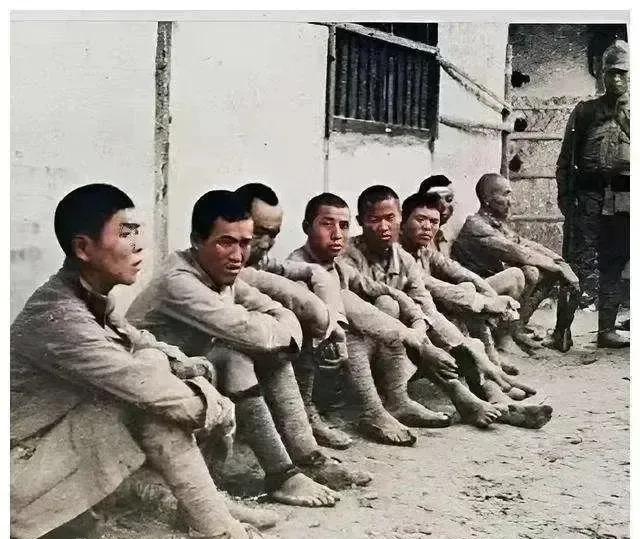





用户10xxx53
战神,名不虚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