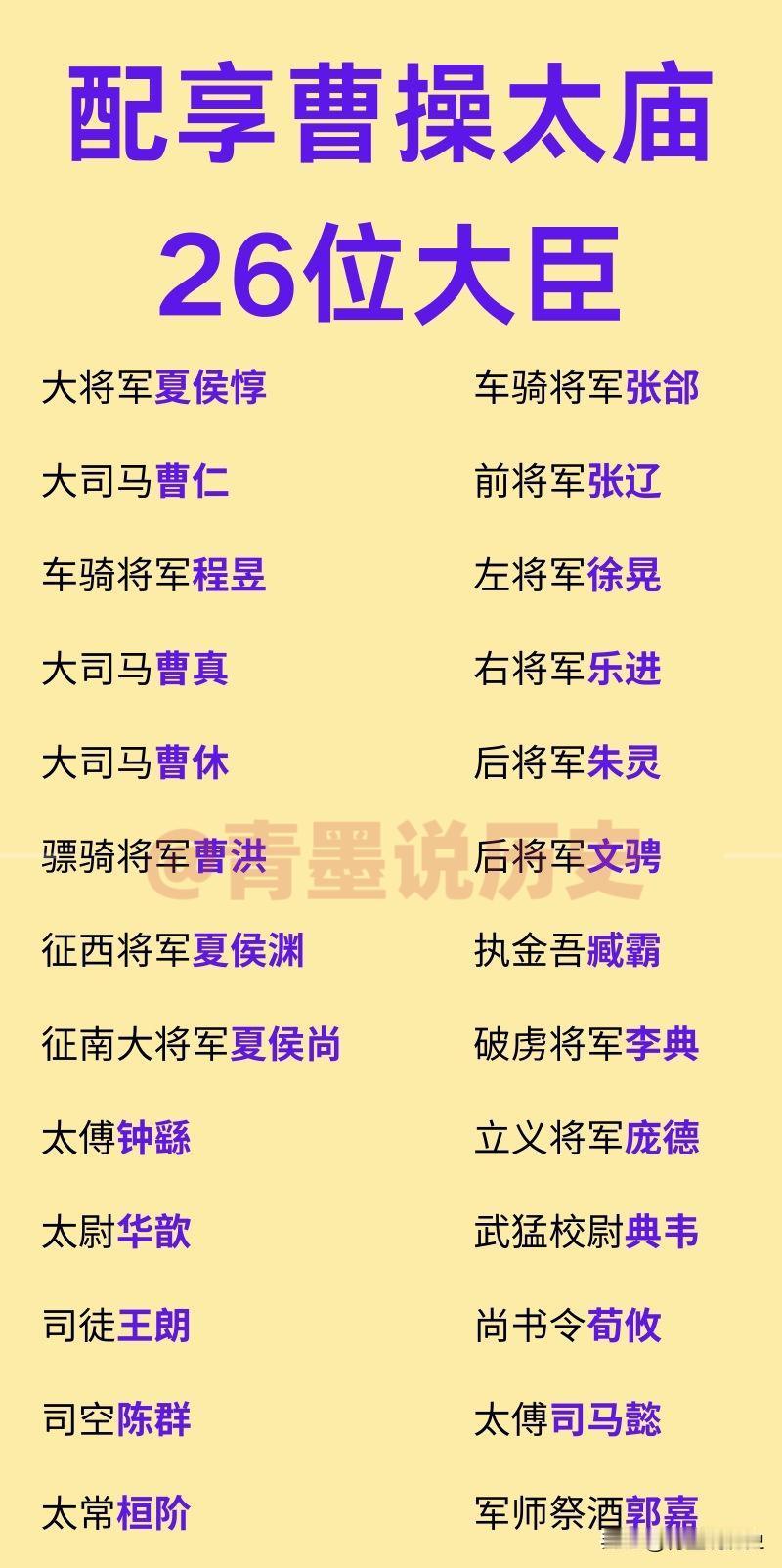曹操究竟想不想扶汉? 少年时的曹操,在洛阳街头用五色棒打死宦官蹇硕的叔父,那时他眼里容不得半点沙子,觉得凭一己之力能澄清吏治。 二十岁举孝廉入朝,三次上书弹劾宦官外戚,甚至在济南国罢免八成贪官,逼得污吏逃到邻郡——这些事若放在太平盛世,妥妥是汉室忠臣的剧本。可东汉末年的朝堂,早已是烂透的木头,他越挣扎,越发现自己像被蛛网缠住的飞蛾。 转折点在董卓进京。当十八路诸侯畏缩不前,只有曹操带着五千人西进荥阳,被徐荣杀得几乎丧命。那时候的他,或许还想着“匡扶汉室”是实实在在的使命。但现实是,袁绍们忙着抢地盘,汉献帝在流亡路上啃草根。直到建安元年,曹操把天子迎到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策略,本质是乱世中的生存法则——没有汉室这块招牌,他一个宦官养子的后代,拿什么号令兖州的青州兵、河北的士人集团? 看看他的《述志令》,早年梦想不过是当征西将军,死后墓碑刻“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可随着兖州牧、大将军、丞相、魏王的头衔叠加,这个梦想像被潮水推远的小船。 屯田制、唯才是举、抑制豪强,这些政策确实让北方百姓吃上饭,让寒门士子有了出路,某种意义上延续了汉室的命脉。 但另一方面,他让荀彧守尚书台,让夏侯惇掌军权,让儿子们都督各州,分明在编织曹家的权力网。汉献帝身边的董承、伏完先后被杀,不是他不知道忠君的道理,而是他清楚,在乱世松开刀柄,就是给全家判死刑。 最矛盾的是他的诗文。《蒿里行》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短歌行》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这些句子里的悲悯与抱负,很难全是作伪。赤壁之战前,孙权劝他称帝,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既不否认野心,又留着汉室的窗户纸。 直到临终,他遗令分香卖履,不提称帝之事,却在《遗令》里反复叮嘱“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这种纠结,像极了一个匠人,明知老屋将倾,仍舍不得放下手中的瓦刀。 或许该换个角度看:东汉末年的汉室,早已是具政治僵尸。曹操不是不想扶,而是扶不起。当他在兖州收编三十万黄巾军时,当他在官渡以两万破十万时,当他在乌桓的风沙中写下“老骥伏枥”时,他的目标早已从“扶汉”变成了“安民”。 汉室的旗号是艘破船,他需要这艘船的名分,更需要用自己的桨把船划出漩涡。荀彧的死,是理想主义的破灭;曹丕的称帝,是现实主义的胜利。曹操的一生,活成了乱世中最真实的矛盾体——他既是汉室的掘墓人,也是汉室的守灵人,在忠与奸的钢丝上,走完了属于自己的独木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