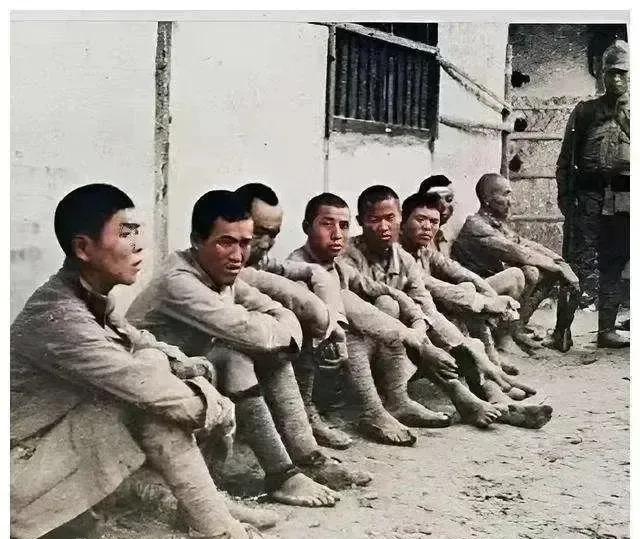1937年,西路军伤员刘克先正在街边讨饭,一个国民党士兵走了过来,上下打量了一眼,说:“以后你就在这里等我,我给你送饭!” 刘克先手里的破碗晃了晃,沿边结着的冰碴子掉进灰扑扑的衣襟——自兵败祁连山后,左腿中枪的他爬了三天三夜才躲进这座小镇,见惯了国民党军队翻箱倒柜的搜查,地主家恶犬撕咬的獠牙,甚至难民为半块发霉的窝头扭打在一起,从未想过“敌人”会对他说出这样的话。 那士兵看着不过二十出头,军绿色的粗布军装洗得发白,右袖口磨出的破洞用同色布条打了个歪歪扭扭的补丁,脸颊上是西北高原特有的、被风沙刻出的红痕。他没多话,从帆布挎包里掏出两个硬邦邦的玉米面窝头,塞进刘克先怀里时,指腹的茧子蹭过他干裂的手背,带着点温热的糙意。 第二天晌午,刘克先抱着最后一丝侥幸蜷在老槐树下,士兵果然来了。这次他用粗瓷碗端着热粥,碗边还放着一小碟切碎的咸菜,声音压得像蚊子哼:“趁热吃,伙房偷的,别让人看见。”刘克先扒拉着粥,眼泪啪嗒掉进碗里,混着米香咽下去,忍不住抬头问:“你就不怕长官知道?” 士兵摸了摸歪戴的军帽,帽檐下的眼睛亮得像星星:“怕啥?我爹也是当兵的,他说不管穿啥衣裳,中国人不能饿中国人。” 那时国共合作的消息已像风一样刮过黄土坡,但镇上城隍庙的墙上,“剿匪通令”的墨迹还新鲜得很,巡逻的宪兵腰间的枪套擦得锃亮,见了穿得破烂的就瞪眼——谁都知道,“合作”在这地界儿,还只是纸上的字。 士兵再来时,揣了个油纸包,里面是晒干的草药。他蹲下身扒开刘克先的裤腿,看着溃烂的伤口皱紧眉头:“这得敷上,不然腿就废了。”刘克先攥着草药,突然觉得心口那团熄灭的火又烧了起来,他不再只想活着,开始盼着士兵说的“赶走小鬼子,说不定能在一条战壕里”的那天。 可这样的日子没撑过半个月。第七天,太阳落山了士兵也没来。刘克先在槐树下等了三天三夜,等来一个叼着烟的哨兵,瞥他一眼随口说:“找那个新兵蛋子?前天被抓了,说是私藏共匪,押去军法处了。” 刘克先的腿一软,瘫在地上。他不知道那士兵叫啥,家在哪儿,甚至记不清他具体长啥样,只记得窝头的温度,说“中国人不饿中国人”时的语气,还有扒开裤腿时,指尖轻轻碰过伤口的小心翼翼。 后来刘克先找到了八路军,重新拿起枪。每次冲锋他都跑在最前面,子弹擦着耳边飞过时,他总觉得那个没名字的兵就在旁边,于是更拼命地往前冲——他得替他多杀几个鬼子。 离休后,刘克先常坐在阳台上,给孙辈看腿上那条歪歪扭扭的疤。阳光照在疤痕上,像一条发亮的蚯蚓。他说:“那年月最黑的时候,是个‘敌人’给了我碗热粥——你看,不管啥时候,人心底的那点好,藏不住。” 孙辈问:“爷爷,要是再见到那个兵,你想对他说啥?” 刘克先摸了摸疤痕,半天没说话,眼里慢慢湿了。 或许啥也不用说。就像当年槐树下那碗粥,不用言语,热乎气儿就能暖透整个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