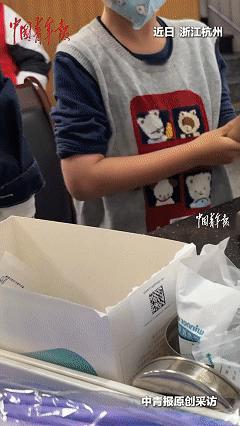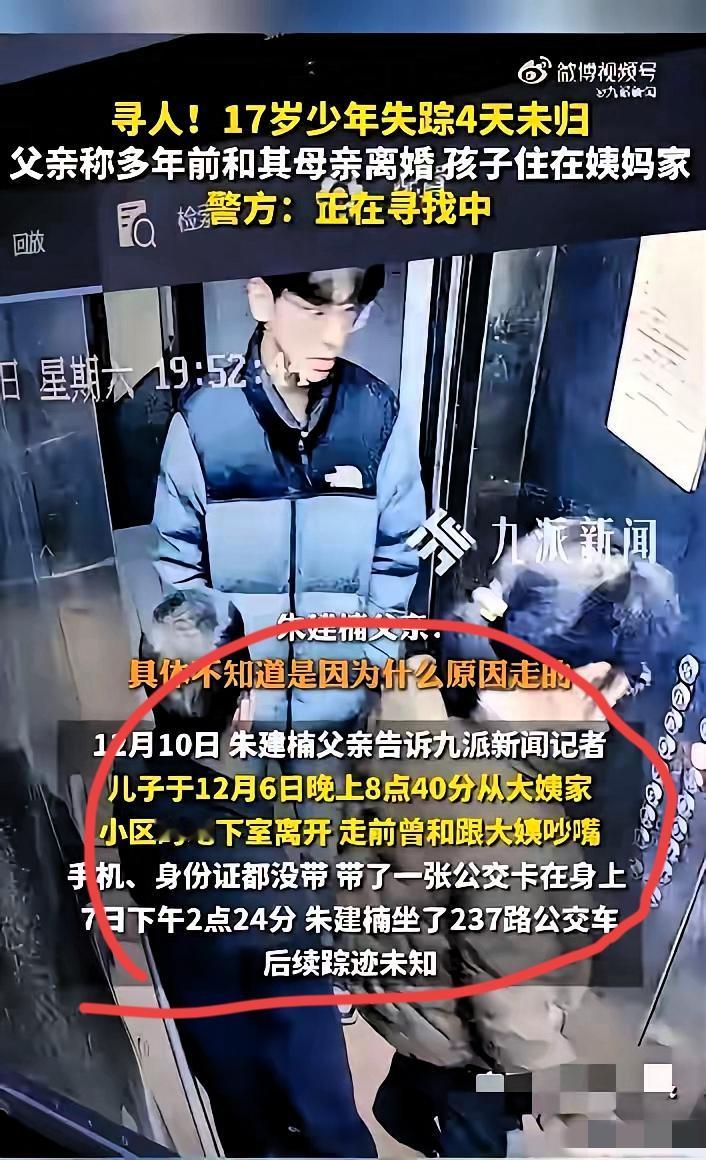工地上的临时夫妻太多了。去年我在西安干活,工地上有一对临时夫妻。他们在工地上干活,白天在一块干活,晚上挤在彩钢房的小单间里,日子过得简单又透着股说不出的无奈。 第二年开春,西安的风还带着凉意,老周已经在彩钢房门口蹲了三天。他手里攥着个磨得发亮的搪瓷缸,缸底沉着半缸凉白开,目光总往公交站台的方向瞟。 老周是河南来的瓦工,快四十的人了,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那是常年搬砖码墙磨出来的。李姐比他小两岁,四川口音,跟着他打下手,搬砖、和灰、递工具,工地上的人都喊她“周嫂子”,她每次都笑着摆手,却从不解释“嫂子”前面的“周”字从何而来。 老家的日子各有各的沉。老周媳妇在河南带俩娃,瘫痪的老娘躺炕上,每月药钱像座小山;李姐男人在新疆摘棉花,三年没回过四川,六岁的女儿跟着奶奶,电话里总问“妈妈是不是不要我了”。 工地上的清晨比鸡叫还早。五点半的天刚蒙蒙亮,李姐已经用冷水洗完脸,塑料袋里裹着俩热馒头,咸菜是她自己腌的,辣丝丝的。老周趿拉着后跟磨出毛边的劳保鞋过来,接过馒头咬一大口,面香混着辣,在嘴里慢慢化——这就是一天的力气来源。 去年秋天有回,李姐接女儿电话时突然哭了。六岁的娃在那头抽噎:“奶奶说你跟别人跑了……”李姐抱着手机蹲在地上,肩膀一抽一抽的,话都说不囫囵。老周在旁边站着,手插在工装裤兜里,半天摸出颗水果糖,剥开糖纸递过去:“给娃说,妈过年带新衣裳回去,带她去县城吃牛肉面。” 更早之前,老周媳妇来电话,说小儿子学费差一千二,老娘的降压药也见底了。他捏着手机蹲在墙根,指节捏得发白,烟一根接一根抽,把小单间熏得像个烟囱。李姐没吭声,从床板下拖出个布包,零钱皱巴巴的,数出一千五塞进他手里:“先拿去,我这儿还有。”老周抬头看她,眼眶红了:“你娃也等着钱买书包。”“她爸会寄的,”李姐把钱往他怀里按,“你这儿等不得。” 第四天早上,公交站台那边终于有个熟悉的身影。李姐背着帆布包,头发扎得紧紧的,朝工地小跑过来,尘土在她脚后扬成一小团。老周猛地站起来,搪瓷缸“哐当”掉地上,水洒了一地,他咧开嘴笑,露出两排黄牙:“来了?”李姐也笑,跑得有点喘:“路上堵车。” 有人说这是胡闹,老家有妻儿还扯这些。可工地上的人都懂,钢筋水泥里的日子,一个人扛着太沉。这样的“临时”,是背叛还是支撑?老周砌墙时,李姐总在下面扶着脚手架;李姐搬砖累了,老周会多歇十分钟等她。不是夫妻,胜似搭伙过日子——谁也没说破,却都在对方身上找着点活下去的盼头。 这些年,工地像个流动的村庄,临时搭伙的男女不少。他们不是不想守着老家的炕头,只是房贷、娃的学费、老人的药罐,把人从家拽出来,扔到千里之外的工地上。白天是钢筋水泥的“建设者”,晚上挤在彩钢房里,才敢卸下那层硬壳。 日子还是老样子,早上啃馒头,中午蹲墙根吃大锅菜,晚上挤小单间。可今年李姐的咸菜里多了点肉末,老周的搪瓷缸里偶尔会泡上枸杞——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却像给苦日子撒了把糖。 彩钢房的墙皮又掉了块,露出里面的泡沫。老周和李姐挤在小床上,听着外面的风声。日子简单,无奈,却也在互相帮衬里,透着点往下走的劲。谁知道明年还能不能一起干活?不知道。但眼下,能有个人递馒头、擦眼泪、一起等天亮,就够了。
“解释不清了!”浙江杭州,一妈妈带孩子去医院抽血,结果,护士刚拿起针,小孩就崩溃
【1评论】【5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