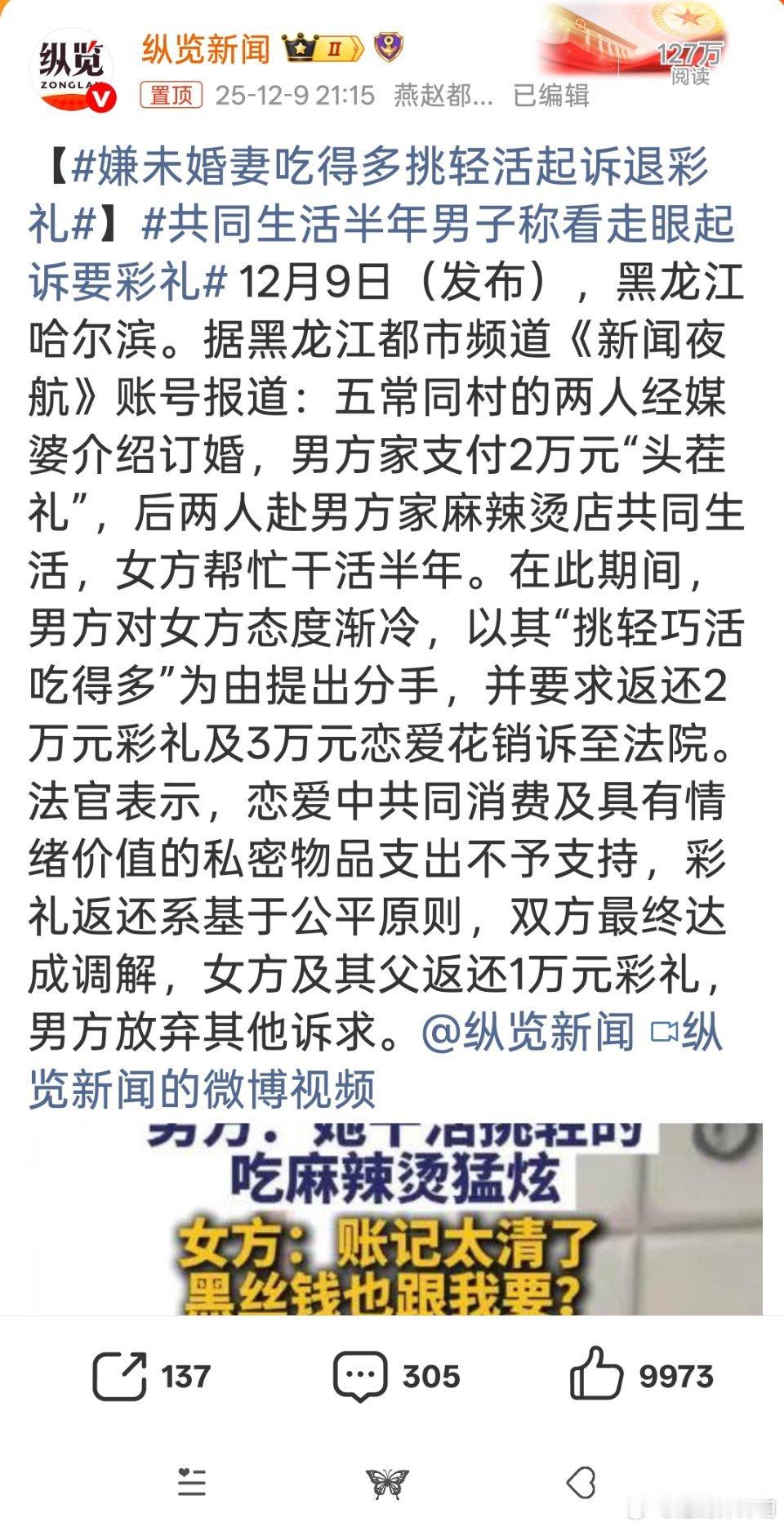在哈尔滨的东北烈士纪念馆里,有一颗头颅。一颗被剜掉了双眼的。这颗头颅的主人,是东北抗联第三方面军总指挥陈翰章,牺牲时刚满27岁。 隔着冰冷的玻璃,那张年轻而残缺的面容,带来的冲击难以言表。他牺牲在1940年最冷的冬天。 那是1940年12月8日,黑龙江宁安镜泊湖边的小弯沟,冷得空气都要冻裂。陈翰章和十几名战友被大批日伪军层层围住,是叛徒出卖了他们的行踪。子弹从四面八方飞来,他们边打边退,直到退无可退。敌人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镜泊英雄”,竟然停止了射击,喊起话来,许他高官厚禄。回答他们的只有一声炸雷般的怒吼:“死也不当亡国奴!”紧接着,机枪喷出最后的火舌。 他的胸口和右手相继中弹,倒在雪地里,血迅速洇开一片刺眼的红。他咬着牙,用尽力气靠着一棵大松树坐起来,还想继续战斗。敌人扑上来,夺走了他的枪。他失去了武器,但还有舌头,还有眼睛。他痛骂,他怒视。丧心病狂的敌人,用刺刀搅了他的舌头,剜出了他的双眼。最终,他们割下了这位年仅27岁指挥官的头颅,装入盛满福尔马林液的玻璃缸,送往伪满的“首都”去邀功请赏。 站在纪念馆里,我很难把玻璃后的面孔,和另一个陈翰章联系起来。那个陈翰章,脸庞应该是清秀的,眼神是温润的。1930年,他从敖东中学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站上讲台,成了一名小学教师。在毕业典礼上,这个众人眼中的“小才子”说,他立志教育救国,培养人才。但他也留下了另一句话:“假如我的理想因为被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打破的话,我一定投笔从戎,用手中的枪和我的鲜血、生命来赶走敌人!”一年后,“九一八”事变爆发,枪炮声打破了他教书育人的梦想。他毫不犹豫,放下了笔,扛起了枪。 这一扛,就是八年。他从一个书生,变成了让日军头痛不已的军事指挥。他带队突袭镜泊湖北湖头的日本水电站,烧了工地,救了劳工,工程硬是搞不下去。他指挥安图大沙河“围城打援”,四天让敌人伤亡五百多。在寒葱岭,他带队埋伏七个多小时,全歼了包括日军少将松岛在内的“讨伐队”。老百姓编了歌谣唱:“日本鬼子遭了殃,出门遇见陈翰章。”从1936年到1940年,有记录的战斗就有81次。日军悬赏五千大洋要他的脑袋,却始终抓不住他。最终,他们用背叛和包围,才困住了这只猛虎。 我一直好奇,在那些冰天雪地、饥寒交迫的密营里,他在想什么?直到我听说他留下了34篇战地日记。这些日记被敌人搜去,反倒成了历史的铁证。里面记着战斗的部署与得失,冷静得像一份份军事报告。也记着伤痛的滋味,1939年春天,他的大腿被子弹贯穿,他写道:“这是我为抗日救国民族军事业流血而无限光荣。”伤口留下了63个针脚的疤痕,他称之为“永久存在的纪念”。 日记里最揪心的,是关于他的父亲。日军抓了他年迈的父亲,逼老人进山劝降。他见到父亲,心里是“莫大的震动”。但谁也不知道,这次危险的会面后,陈翰章的父亲,竟然成了为抗联秘密传递情报的交通员。家与国,在那一刻以最隐秘又最壮烈的方式,紧紧绑在了一起。这些日记,写在一张张可能被冻硬、被血迹沾染的纸上,是一个年轻灵魂在绝境中留下的最真实的呼吸。它们比任何纪念碑都更有力,告诉我们英雄不是天生的钢铁,而是一个个做出了坚定选择的、有血有肉的人。 陈翰章的头颅在东北烈士纪念馆静静陈列了许多年。直到2013年,他诞辰一百周年的时候,人们才将他的头颅迎回吉林敦化的故乡,与遗骨合葬。他出生的小村子,如今叫翰章乡翰章村。村边建起了庄严的烈士陵园,里面有一座2.7米高的雕像,象征着他27年的璀璨生命。2024年,陈翰章生平事迹文化中心在村里成立,讲解员对来访者说:“笔墨可以化为刀剑,书生亦能成为脊梁。”孩子们在叫作“翰章红军小学”的校园里奔跑,操场边就立着他的雕塑。 从被悬赏追捕的“匪”,到被万众景仰的“英雄”,这条路他走了八年,而他的民族走得更久。有时候我会想,我们今天如此隆重地纪念他,究竟是在纪念什么?是纪念那具被残忍伤害的躯体吗?不完全是。我们纪念的,是那份在黑暗里比灯光更刺眼的清醒,是那个在冰封大地上比火种更滚烫的选择。一个文明的延续,不仅依靠丰饶的物产,更依赖一代代人记忆中那根不肯弯曲的脊骨。他的头颅曾经被敌人当作战利品展示,如今,却成了我们精神上最沉重的、也最不可摧毁的纪念碑。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肥胖关键时刻也保命[捂脸哭]近日,黑龙江省哈尔滨一300斤女孩和家里发生争吵,女](http://image.uczzd.cn/1775884460481154341.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