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命,我选择不和任何人接触,我现在情绪稳定,心里非常平静。医生说这是重度焦虑引发的应激障碍,得“减少刺激源”。于是我辞了职,把自己锁在租来的一居室里,外卖地址填在楼下快递柜,电话设置成“仅联系人可见”,连窗帘都换成了遮光款。最初的日子确实清净,不用应付客户的刁难,不用听同事的闲言碎语,不用在聚餐时强装笑脸,夜里也不会突然惊醒——那些曾经让我崩溃的“噪音”,都被关在了门外。 医生在诊断书上写“重度焦虑应激障碍”时,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比我当时的心跳还稳。他说要“减少刺激源”,我把这句话刻进了脑子里——像给生锈的门锁换了把新钥匙,咔嗒一声,世界就被我关在了门外。 辞了职的那天,我把工位上的多肉扔进垃圾桶,那盆被我养得只剩两片叶子的植物,和我一样,早就不适合见光了。回到租的一居室,第一件事是换窗帘,选了最深的藏蓝色遮光款,拉严时连空气都暗了三分,缝隙里漏进来的光,像被掐断的线头,蜷在地板上一动不动。 外卖地址设成楼下快递柜,备注栏写“放柜里,别打电话”;手机调了“仅联系人可见”,而联系人列表里,除了120和外卖平台客服,空得能听见回声。最初的一周,我甚至爱上了这种安静:不用在早高峰的地铁里被人挤成相片,不用对着客户的夺命连环call赔笑脸,夜里不会突然坐起来盯着天花板发呆——那些曾经像针一样扎进我神经的“噪音”,真的被挡在了门外。 直到第三周的周二,雨下得很大,我踩着积水去取外卖时,看见快递柜旁蹲着个阿姨,正把被雨淋湿的纸箱往塑料袋里塞。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透明胶带“啪”地断了,“小伙子,你这伞也太小了,”她指了指我手里那把折叠伞,伞骨歪了两根,伞面破了个洞,雨水顺着洞眼往下滴,在我鞋面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我往后缩了缩,想绕开她,她却站起来,从塑料袋里掏出个东西递过来:“刚蒸的红糖馒头,热乎的,你外卖盒都湿了,先垫垫?”是个用保鲜袋裹着的馒头,热气透过袋子漫出来,在冷雨天里像团小小的云。 我没接,喉咙发紧,手指攥着伞柄用力到发白。她怎么会跟我说话?她不知道我不能被打扰吗?这些念头像野草一样疯长,可看着她递过来的手,关节处有块浅褐色的疤痕,指甲盖边缘修剪得整整齐齐,我突然想起我妈——我妈以前给我送馒头时,手背上也有块烫疤,是给我煮面时被溅的油星子烫的。 “拿着吧,”她把馒头往我怀里塞了塞,保鲜袋的温度透过卫衣布料传过来,暖得我打了个哆嗦,“老吃凉外卖对胃不好,我住三楼,姓王,你叫我王阿姨就行。”说完她又蹲下去收拾纸箱,好像刚才只是随手递给邻居一颗糖。 那天的红糖馒头,我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甜得有点发苦,却让我想起很多年前,我妈在厨房蒸馒头时,蒸笼冒的白汽,在窗户上凝成水珠,顺着玻璃往下淌,像谁在哭。 晚上躺在床上,我第一次没有拉严窗帘,留了条一指宽的缝。路灯的光从缝里漏进来,在墙上投出一条细长的亮线,像根没拉满的弓弦。我盯着那道光看了很久,突然想问自己:医生说的“减少刺激源”,是让我把所有光都挡住吗? 这周的外卖备注,我改成了“如果王阿姨在,麻烦告诉她馒头很好吃”。昨天取外卖时,快递柜上贴了张便签,是用红笔写的:“明天蒸南瓜包,要几个?”字迹歪歪扭扭的,末尾画了个笑脸,嘴角却画得有点斜,像个没画好的月亮。 我站在原地,摸了摸口袋里的手机,联系人列表还是空的,但我突然想,或许可以把王阿姨的电话存进去——就存成“南瓜包阿姨”,这样下次她再递馒头时,我至少能说声“谢谢”,而不是像个不会说话的石头。 窗帘缝里的光,好像比昨天宽了一点点。
医生轻飘飘一句“一片方便些”,我心里咯噔一下,差点没绷住。天知道为了这“一片”
【1评论】【1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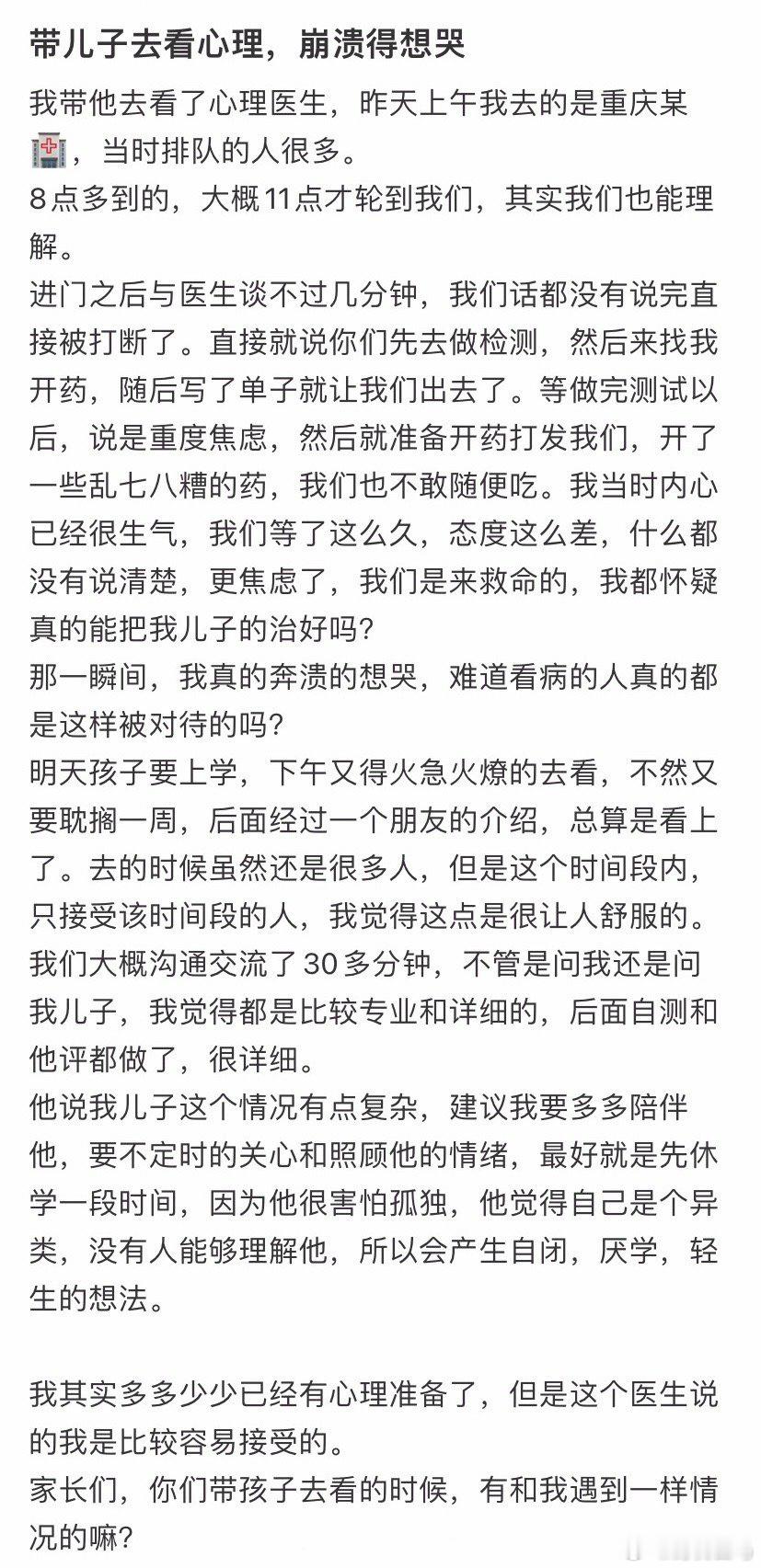







fei
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