窦文涛说:“我在医院守夜,看到家属逼着医生拔管子,医生说心跳还有30多下,为什么拔管子?家属却说:‘你给我拔了,这算是死了!不是无情,是真的没钱了。’”这话听得我心里发沉。想起前几年在医院陪护时,见过个类似的事。病房里住了位姓赵的大爷,七十多了,脑溢血昏迷半个月,每天靠呼吸机维持。 消毒水的味道像层膜,糊在鼻尖上,甩都甩不掉。我那年在医院陪护,住对床的是赵大爷,七十多,脑溢血昏迷半个月,呼吸机管子从嘴里插进去,每口气都带着“嘶嘶”的响。 他儿子总坐在床边,蓝布褂子洗得发白,袖口磨出毛边。手里捏着张缴费单,指节捏得发白,我瞥见过一眼,数字后面好几个零,像串扎人的刺。 头几天他还跟医生搭话,问“还有希望不”,医生说“不好说,得看水肿消得怎么样”。后来医生再来,他就光点头,不说话了,眼睛盯着监护仪——绿线一跳一跳,像根绷紧的弦,每跳一下,隔壁床的呼噜声、走廊的脚步声、护士换液的轮子声,都像被按了暂停键。 有天半夜我起夜,看见他趴在床边,握着赵大爷的手。赵大爷的手枯瘦,他的手糙得像砂纸,摩挲着爸手背的老年斑,小声说:“爸,对不住了。”声音轻得像蚊子哼,可我听得心揪了一下。 第二天一早他去找医生,我跟到走廊口,听见医生叹口气:“再观察两天?昨天瞳孔对光还有反应……”他没让医生说完,摇摇头,说:“不了,他也累了。”——我看见他手在抖,不是害怕,是使劲攥着拳头,怕自己哭出来。 护士来撤呼吸机时,隔壁床的阿姨凑过来跟我嘀咕:“这儿子心够狠,万一醒了呢?”我没接话,转头看见他站在楼梯间,背对着我,想抽烟,摸出烟盒,空的,又塞回去。打火机“咔嗒”响了三次才打着,烟叼在嘴里,没抽,先掉了眼泪,砸在水泥地上,晕开一小片湿。 你说这世上最疼的,是眼睁睁看着亲人受苦,还是连让他“体面”离开的钱都凑不齐?我后来才知道,他开货车跑长途的,攒了三年的钱想给儿子娶媳妇,半个月全填进了ICU;媳妇把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妹妹把给孩子报补习班的钱打了过来,还是不够——每天八千多的费用,像个无底洞,吞了钱,也吞了他眼里最后点光。 撤机那天下午,监护仪的绿线慢慢拉成直线,“嘀——”的长音里,他给赵大爷擦了脸,梳了头发,动作轻得像怕碰碎个瓷碗。以前听人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那天我看见,他给爸穿鞋时,手指在爸脚踝上停了停,那里有个小时候被自行车夹的疤,他小时候总摸那个疤撒娇,说“爸你看,跟月牙似的”。 现在窦文涛说的那句“不是无情,是真的没钱了”,突然就有了形状。是蓝布褂子袖口的毛边,是捏皱的缴费单,是打不着的打火机,是楼梯间没抽成的烟。 后来我再路过那家医院,消毒水味还是那么冲,可总想起赵大爷儿子站在窗边的背影。他没哭出声,肩膀一动一动的,像株被雨打蔫的玉米——不是撑不住,是真的,再没力气撑了。 有些告别,不是不爱,是爱到只能放手。你说,这世上的无奈,怎么就这么沉呢?
痛心!太快了,妻子下雪出去溜达玩,突然不小心后脑勺着地,当时摔的人不会吭声了,双
【11评论】【8点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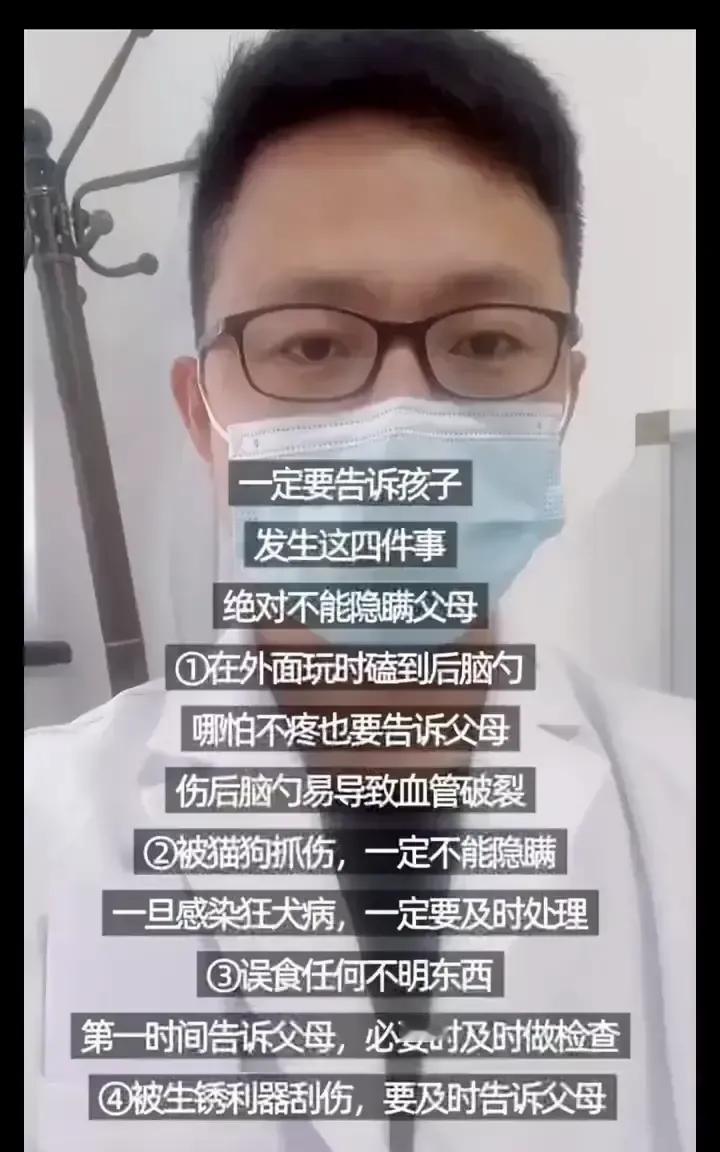
![大爷人不错,救了小伙子一辈子啊[吃瓜]](http://image.uczzd.cn/12265433899936344615.jpg?i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