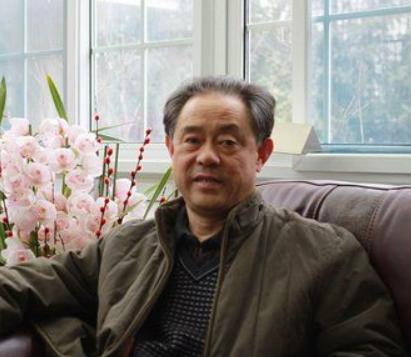民国船夫的沧桑:五十岁的年纪,八十岁的面容 民国时期,一名船夫坐在船上休息。船夫五十岁的年龄却有着八十岁的面容。他的面容与年龄极不相符。这也是过去最常见的现象。尤其那些重体力劳动者只要上了四十五岁看起来就像七八十岁的老人。 这位船夫姓陈,名老根,在苏州河上撑船撑了整整三十五年。江南的水汽裹着河风,日复一日吹在他脸上,把皮肤揉得像泡发的老树皮,眼角的皱纹深得能夹住河面上漂来的草屑,手背的筋络像老树根一样盘虬着,那是常年握着船桨磨出来的硬茧和劳损。 他总说自己记不清确切生辰,只知道从十三岁跟着父亲学撑船起,就没过上一天松快日子。父亲走得早,十五岁的他接过那支磨得发亮的榆木船桨,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母亲卧病在床,两个妹妹等着吃饭,船桨一撑,就是半辈子的责任。 民国二十二年的苏州河,远没有后来的繁华,河面上来来往往的多是运货的驳船和讨生活的小篷船。陈老根的船是条窄窄的乌篷船,船头磨掉了漆,露出木头的原色,船底还漏着缝,得用麻絮混着桐油天天补。 他每天天不亮就得起身,先去码头接那些赶早市的商贩,或是载着过江的行人,从城东到城西,一趟下来能挣两个铜板。可这两个铜板,一半要交给码头的把头,剩下的还要买糙米和母亲的汤药,往往和母亲的汤药,往往刚到晌午,兜里就空了。 为了多挣几个钱,他常常撑船到深夜,哪怕遇上刮风下雨,只要有人喊船,他就不敢歇。有年冬天,河面结了薄冰,他为了接一个赶急事的客商,赤手去掰船桨上的冰碴,手指冻得肿成萝卜,直到开春都没消肿,从此一到阴雨天,指关节就钻心地疼。 重体力活计耗的是身子骨,可陈老根连口饱饭都吃不上。他的午饭永远是一碗糙米饭配着咸菜,偶尔能在码头捡些商贩掉的烂菜叶,就算是改善伙食。 有次他看着船上的客商啃着白面馒头,咽了咽口水,客商随手扔了半个吃剩的馒头,他捡起来擦了擦,掰成小块喂给了趴在船板上的老黄狗——那狗是他唯一的伴,也是跟着他在河上挨冻受饿的主。 他总说,狗都比他强,至少不用交那苛捐杂税。民国的税目多如牛毛,码头税、船税、人头税,但凡能叫上名的,都要从他那点微薄的收入里扣。有回他实在凑不齐税钱,被把头带人把船桨没收了,他跪在码头的泥地里求了一下午,最后把母亲陪嫁的银簪子抵了,才把船桨赎回来。那夜他坐在船上,抱着船桨哭了,不是哭自己委屈,是哭对不起母亲,哭自己连支船桨都护不住。 四十五岁那年,陈老根的背开始驼了,原本挺直的腰杆被船桨和生活的重担压成了一张弓。他的视力也越来越差,傍晚撑船时,常常看不清对面的来船,好几次差点撞上去。同行的老船夫劝他歇一歇,他摇着头说:“歇了,我那瘫在床上的老母亲,还有嫁不出去的妹妹,喝西北风去?”可命运没放过他,第二年母亲走了,妹妹被婆家嫌弃穷,嫁过去没半年就被赶了回来。 他撑船的劲头更足了,却也老得更快了——头发全白了,脸上的褶子密得像筛子,走路时腿也开始打颤,五十岁的人,走起路来比八十岁的老人还蹒跚。有个路过的洋医生看到他,摇着头说他的身体机能已经严重老化,长期的超负荷劳作、营养不良和慢性疾病,让他的身体提前透支了几十年。可陈老根听不懂什么叫“机能老化”,他只知道,只要船桨还能撑动,他就不能停。 在民国的底层社会里,像陈老根这样的重体力劳动者比比皆是。码头的搬运工,四十岁就弯了腰;拉黄包车的车夫,三十五岁就走不动路;打铁的铁匠,四十岁就握不住铁锤。他们没有劳保,没有医疗,甚至没有基本的温饱,唯一的依靠就是自己的一身力气。 可力气总会被耗尽,当身体被日复一日的劳作掏空,衰老就成了必然的结果。他们的面容,是民国底层民众生存状态的真实写照——那不是自然的老去,是被生活的重负压出来的沧桑,是被时代的苦难刻下的痕迹。 这些底层劳动者用自己的血汗撑起了民国社会的运转,却连基本的生存尊严都难以获得。他们的早衰,从来不是个体的偶然,而是时代的必然。当一个社会的底层民众连温饱都成问题,连身体的基本损耗都无法弥补时,这样的“未老先衰”,就成了刻在一代人脸上的印记。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