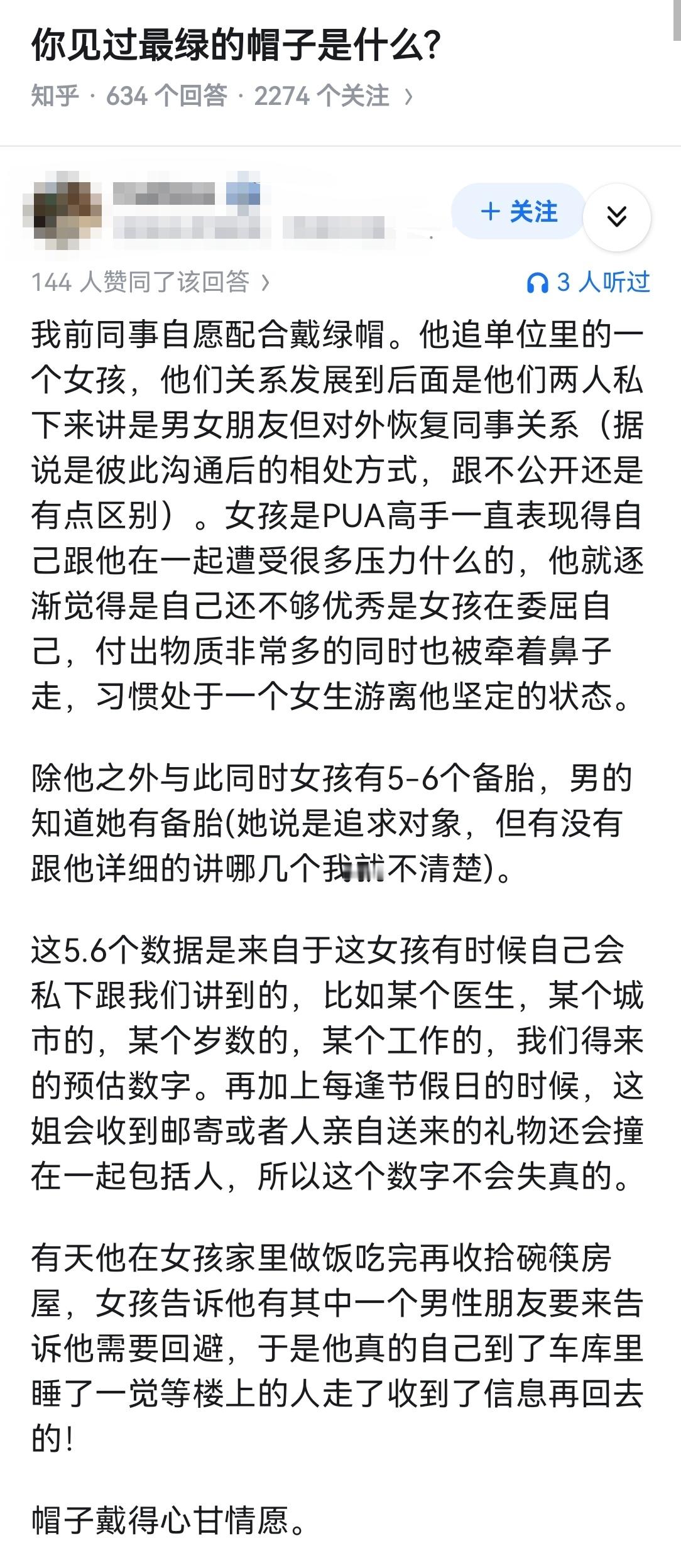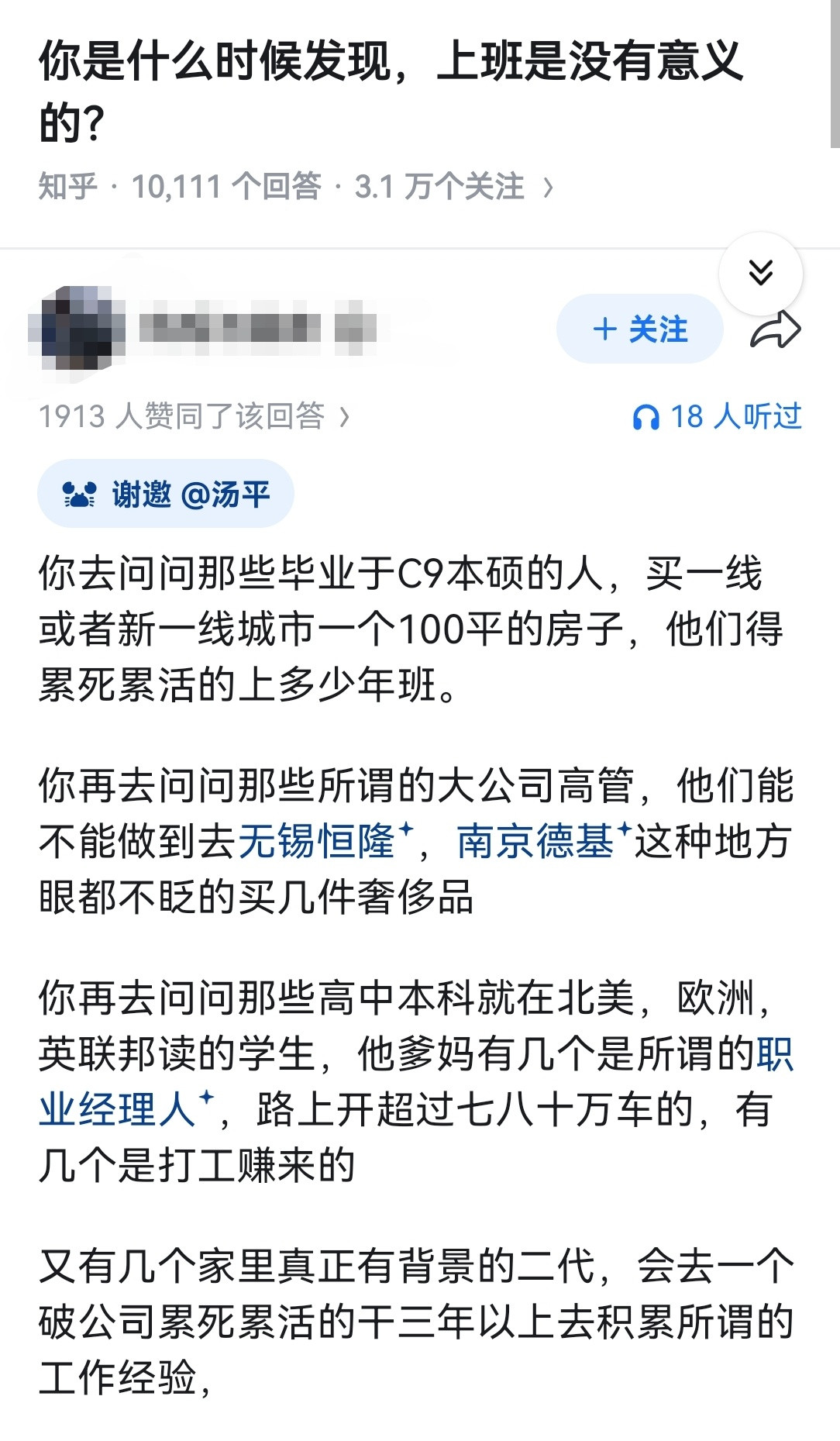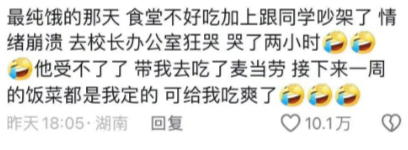我们和二姑已经十年没有来往了,早上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二姑父去世了,叫我去随礼,并且钱不能随少了,我说既然已经不来往了,为什么还要我去随礼?电话那头传来父亲剧烈的咳嗽声,像是要把肺都咳出来:“你二姑......这些年不容易。” 手机在床头柜上震第三下时,我才摸起来——屏幕上“爸”字的备注,像蒙了层灰,和二姑家那个尘封十年的号码一样。 早上七点,窗外的麻雀刚落在晾衣绳上,我还没来得及揉开惺忪的眼。 我们和二姑,整整十年没说过一句话了。 听筒里传来父亲的声音,比记忆里哑了三分,带着清晨未散的凉意:“你二姑父,走了。” 我捏着手机的指节泛白,十年前摔门而出的画面突然冲进脑子里——二姑叉着腰站在堂屋中央,说“这门亲戚不认也罢”,我妈红着眼拉我走,从此两家的春联再没贴对过门。 “既然不来往了,随礼做什么?”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抖,像被风刮着的纸片。 电话那头突然没了声,只有粗重的呼吸,然后是剧烈的咳嗽,一声接一声,像破旧的风箱在拉扯,我甚至能想象出父亲弓着背、手撑着桌沿的样子,咳了半分钟才停,声音哑得像含了沙:“你二姑……这些年不容易。” 挂了电话,我坐在床边发愣。十年里零星听过邻居说,二姑父爱赌,家里的积蓄被输光,二姑白天在工地搬砖,晚上给人缝补衣裳,有次下雨摔断了腿,都是自己咬着牙去的医院——这些事,我爸大概早就知道,只是从没对我们提过。 父亲那句话像根针,轻轻挑开了十年的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二姑总把糖藏在口袋最里层,见我就掏出来,糖纸被体温焐得发软;想起她送我的花布书包,边角磨破了,我还背了三年。 我去银行取了钱,比往年随亲戚的份子多包了两倍。 有些疏远不是因为恨,只是被生活的难困住了脚步。 再远的亲戚,也别让一句“不认”堵死了回头的路。 去二姑家的路上,风卷着纸钱的灰飘过来,落在我鞋尖。二姑站在门口接人,头发全白了,背比我妈还驼,看见我时愣了愣,眼圈突然红了,想说什么又没说,只是往我手里塞了个还温着的煮鸡蛋——和十年前一样,蛋白剥得干干净净。
我们和二姑已经十年没有来往了,早上我爸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二姑父去世了,叫我去随礼
正能量松鼠
2025-12-30 20:42:10
0
阅读: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