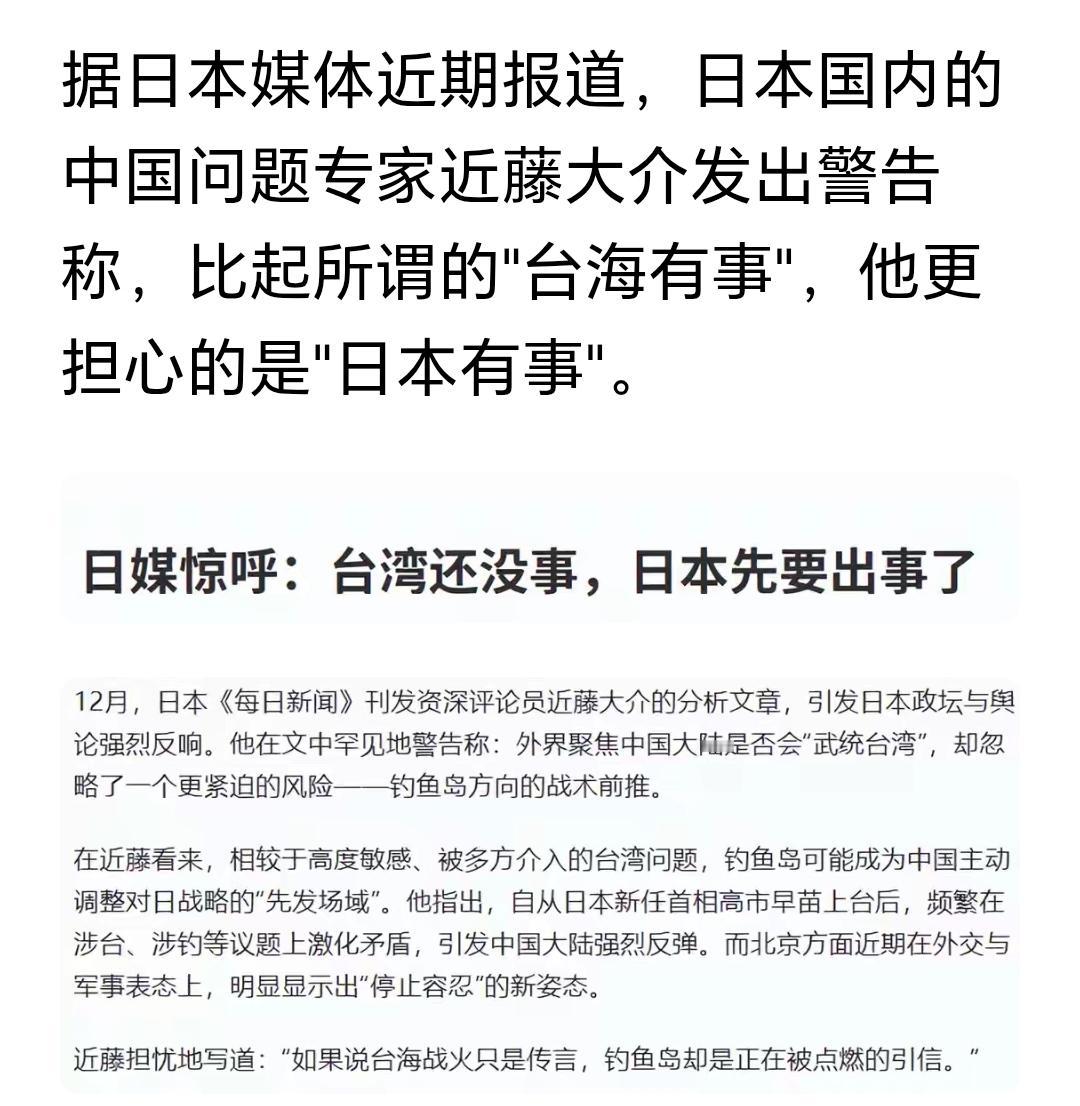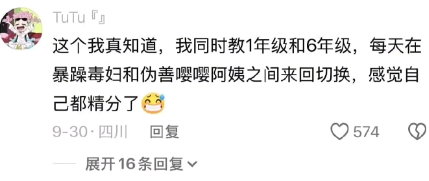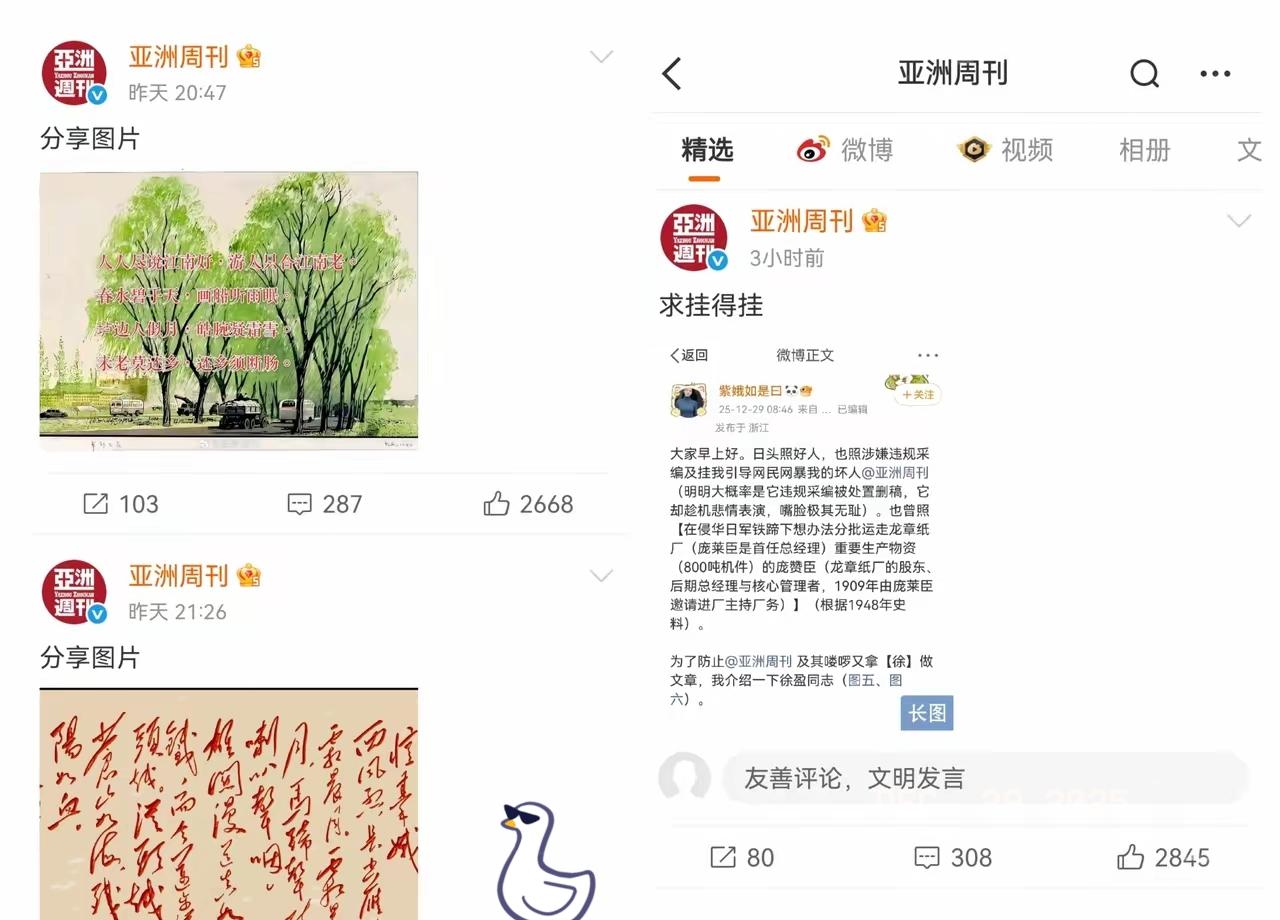1970年,年轻时的莫言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姑娘不屑的说:“癞蛤蟆想吃天鹅肉!”莫言没有放弃,请媒人去提亲,姑娘让媒人给莫言带了一句话,直接影响了他一生! 麻烦各位读者点一下右上角的“关注”,留下您的精彩评论与大家一同探讨,感谢您的强烈支持! 上世纪70年代初的山东高密,田野里的风带着泥土和青草的味道。 一个瘦高的青年,怀里揣着本旧书,正沿着乡间土路往邻村走。 他叫莫言,那时候还是个放羊娃,因为家里穷,很早就辍学了。 但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去邻村一位石匠家借书。 石匠不算文化人,但不知怎的家里却收着不少书,这在高密东北乡的村庄里,算是件稀罕事。 石匠家的院子总是堆着些未完工的石料,空气里飘着石粉的干燥气味。 莫言来这里,起初只是为了那些书。 一来二去,他和石匠的女儿熟络起来。 姑娘也爱看书,两人常常就着书里的故事能聊上好一会儿。 午后的阳光穿过院子里的槐树,落在泛黄的书页上,也落在年轻人渐渐萌动的心事上。 借书、还书,成了莫言那段清苦青春里一抹亮色,也让他对那个爱读书的姑娘生出了一种朦胧的好感。 终于有一天,莫言鼓起勇气,不再仅仅满足于谈论书里的世界。 他托了媒人,正式上门提亲。 这在那时的农村,是再正经不过的程序。 然而,回应却像一盆凉水。 石匠家没看上这个家境贫寒的放羊青年。 更让莫言心头一刺的,是姑娘托媒人带回的那句话。 话的大意是,如果他莫言能写出《封神演义》那样的书,这事才有得商量。 《封神演义》正是莫言从石匠家借出的第一本书,他翻来覆去读过好多遍。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个拒绝的托辞,带着几分调侃,甚至一丝轻视。 在那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环境里,写作成家,对一个小伙子来说,听起来像个不切实际的梦。 但这句话,偏偏像颗种子,掉进了莫言心里那片渴望生长的土壤。 它没有立即开花结果,却悄悄地改变了某些东西。 放羊的时候,躺在山坡上看着云卷云舒,他开始不止于幻想故事里的神魔斗法,脑子里也会冒出一些属于自己的、关于脚下这片土地的模糊片段。 他尝试着把这些零碎的想法记下来,虽然笔触稚嫩,前路迷茫。 人生的转折有时来得意外。 1976年,莫言参军离开了家乡。 部队的生活规律而开阔,给了他更多时间和空间去读书,去沉淀。 窗外是嘹亮的军号与整齐的步伐,窗内是一个青年对文学世界的默默叩问。 1981年,他的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了。 当印成铅字的文章拿在手中时,他或许会想起多年前那个午后,那句关于《封神演义》的话。 那颗种子,终于在时间的浇灌下,破土而出。 而当年那个借书给他的姑娘,早已成了前尘往事里一个淡淡的影子。 莫言后来娶了在棉纺厂认识的姑娘杜勤兰。 她不识字,但勤劳朴实,用双手稳稳地托住了莫言那个充满文字与想象的、有些“不接地气”的世界。 这份踏实的感情,与他早年的那段无果的暗恋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他人生与创作中复杂的情感底色。 从此,莫言手中的笔再也没有停过。 他把高密东北乡的红高粱、沼泽地、牲口棚,把饥饿的记忆、荒诞的见闻、坚韧的乡民,统统化成了澎湃的文字。 《红高粱家族》里那片如火的血海,《丰乳肥臀》中承载苦难的土地,《生死疲劳》里六道轮回的奇想,一部接一部,轰动了文坛,也让他从山东高密走向了世界。 2012年,当莫言在斯德哥尔摩接过诺贝尔文学奖奖章时,世界的聚光灯打在他身上。 那一瞬间的辉煌,与数十年前那个在乡间土路上揣着旧书、心事重重的青年身影,形成了奇妙的呼应。 没人能预料,一句来自青春时期的、略带刺激的戏言,竟会像一道隐秘的轨迹,牵引着他穿越漫长的岁月与无数的稿纸,最终抵达这里。 莫言的故事,就像他笔下的许多故事一样,带着泥土的朴实与命运的玄妙。 它讲述了一个人如何被一句话点燃,然后凭借持久的热爱与努力,将微弱的火星呵护成燎原的火焰。 它告诉我们,有时候,改变一生的契机,就藏在某个看似不经意的瞬间,等待着被一颗敏感而执着的心捕捉,并在岁月的耕耘中,生长出谁也未曾预料到的、丰硕的果实。 主要信源:(中国网教育——莫言15岁那年,跟邻村一个姑娘表白,姑娘却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随后提了一个要求,改变了莫言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