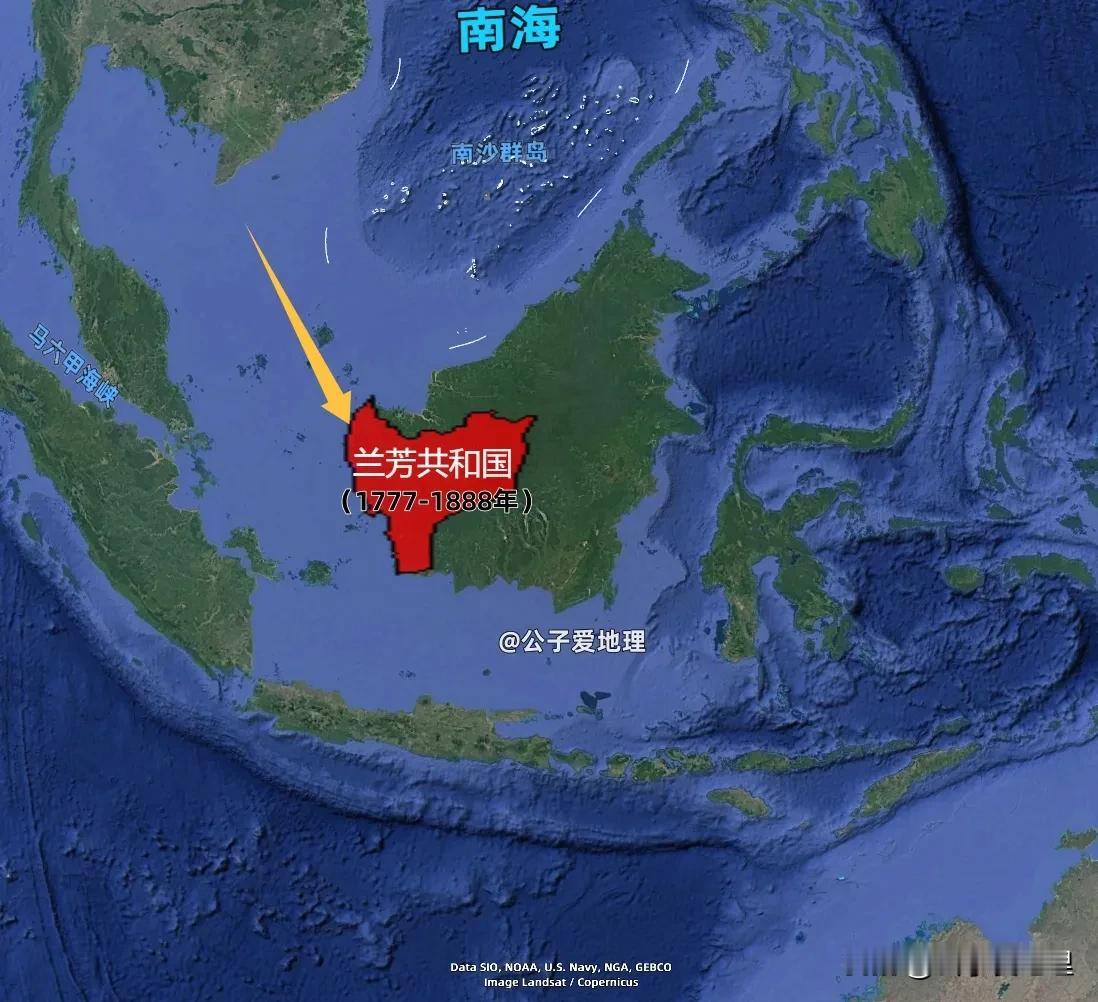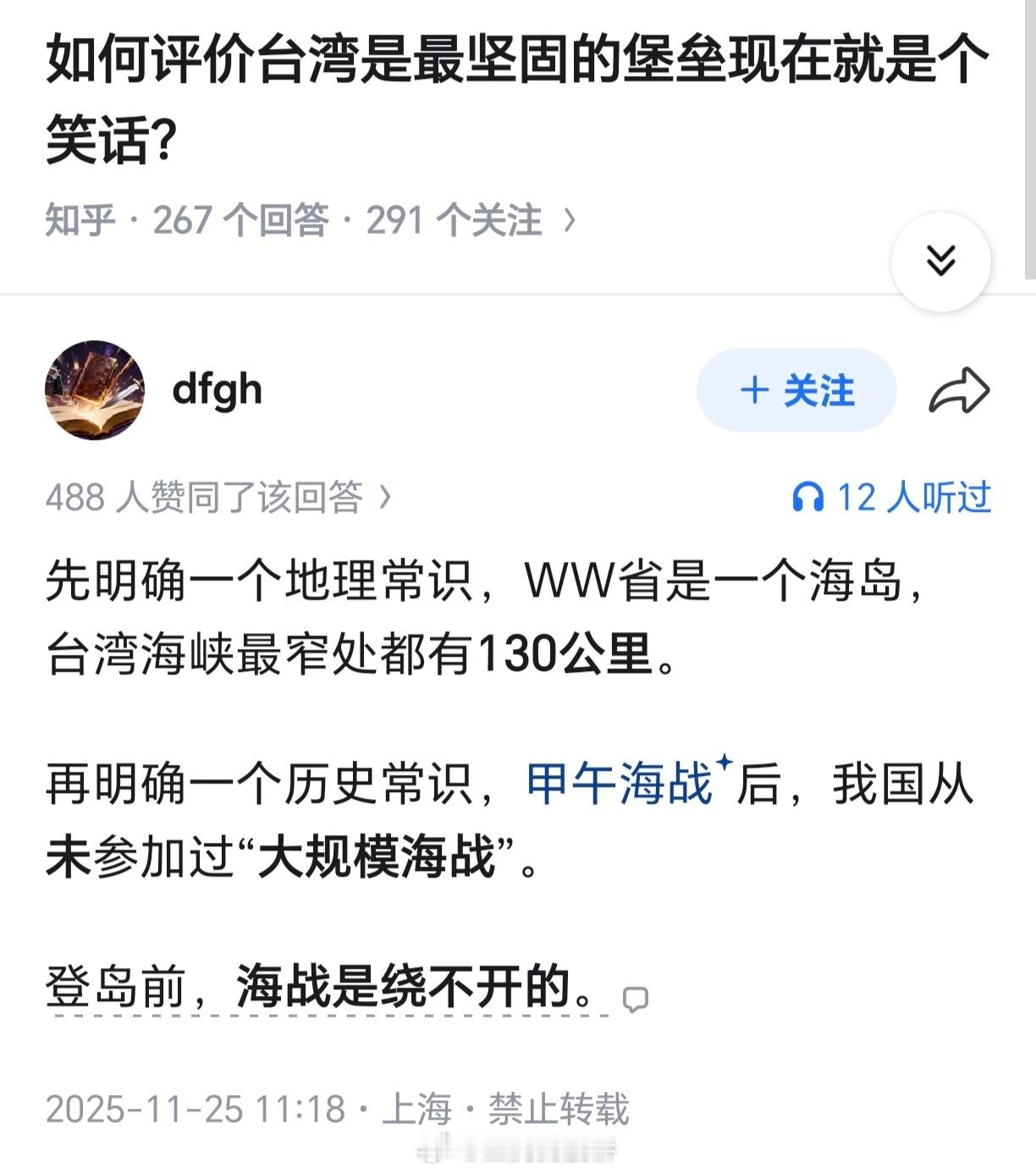1979年,台湾老兵瞒着妻儿寄钱给大陆的原配,没想到,原配居然跟以前的下属“同居”66年了。 1979年,第一封信终于飘到了对岸,但对一个叫易祥的台湾老兵来说,这封信带来的,不只是问候,还有一场推翻“想当然”的情感地震。 那年冬天,台北街头下着雨,易祥手里攥着笔,犹豫了很久。 他给大陆的陈淑珍写了一封信,简单说了自己在台湾的情况,娶妻、生子,还有,这些年攒下了一些钱,想每年寄点回去。 他甚至在信里坦白,如果她觉得孤单,可以和庹长发结婚,活得安心、体面些。 写完,他沉默了十秒才封口。没想到,这封信一抛出去,砸的是家,裂的是心。 得说清楚前头的事,得从1949年码头那声“撤!”,讲起。 那年,一批批国民党官兵仓皇南撤,“走慢的就留着守家”,易祥就是在那种慌乱中,从重庆码头上船的。 他不敢带老母老妻,只带了军帽和命令。最后那句命令,是留给庹长发的:“家,我交给你了。” 庹是四川人,识得几个字,能写能算,还是他的勤务兵。 部队里人多嘴杂,只有庹长发最懂分寸。 庹长发没走。他拖着陈淑珍、抱着孩子,活进了一间坍了一半的破屋。 三年困难时期,白天抢地里最后一点苞谷,晚上摸黑下山找野菜。 有一年冬天滑入山沟,摔断腿,落下终身残疾。他没和人说过,怕是拖陈家后腿。 那个年代,没有解释,只有流言。乡下就是一张嘴,周围人都说他们俩“过一起了”。 可只有他自己知道,每晚收工后,他在厨房铺凉席睡地头。房间里,是陈太太和小少爷的世界。 有人笑他傻,明明一个寡妇守着一个壮汉,“你不干,她也会饿死”。 他没吭,只在烧水的时候握紧拳头:长官是长官,太太是太太,我不能乱。 多年后,一纸家书飞过海峡,当初那个托孤的命令,现在成了复杂的自我救赎。 易祥不只是寄件人,他还偷着寄钱。可他没想到,如今的陈淑珍,已不是当年那个打着粗辫子的米店伙计,而庹长发,也不是那个战战兢兢的小兵。 他俩,所谓“同居”,在别人眼里是勉强生活,在他们心里是守规矩。 易祥在台湾,过得不算差。搞了个小纺织厂,儿女成行,虽然不是大富大贵,但也有面子。 可他最怕的,就是多年后回大陆“认亲”,老街坊拿大巴掌拍他:你跑了,还想回来认祖宗? 但事情卡在这了。他以为两人“早该结婚”,结果一提出,俩人都拒了。 庹长发咬着牙回了信,整整两页,他说,长官当年托付之重,他铭记在心,若真要结婚,那便是脱了这层名义,换个身份亲近,这叫“越界”。 有人说听不懂这套,但老人明白,这是战时伦理在和平年代里的“孝道延续”。 不是说非要礼法过头,而是那个年代的老兵,还活在“承诺当命”的逻辑里。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一出,两岸通信开始松动,但第一批信件的送达率不到三成,不少信卡在边境、卡在审查、卡在“身份不明”的名字里。当时能顺利寄到那封信,就已经是天意。 易祥说:"庹长发不是我兄弟,是全家都欠他命的恩人。" 他也不是嘴上说说,他试着替对方安排新身份,帮他从“家庭帮工”变成“正式丈夫”,甚至还物色过介绍人,只差入户口。 庹长发摇头。这头摇得像水壶嘴,低声说了句:“碗能换,人换不得。” 作为长年的接受方,庹一直吃着易祥的钱,却不曾为自己出过一次名。 他有机会正名,反而退了。他觉得:“我是管好这个家,没资格占这个家。” 今时今日,两岸往来早已不像当年那样,要偷偷传话、步步审查。 但回看那封信的犹豫,还有那段不谈情的守护,才明白,所谓信义,在现在社会流转成了合同和权利,是纸上的东西。 而在他们那一代人,是扛在肩头、磨在骨头上的概念。 信息来源:战友1949年去了台湾 老兵照顾嫂子66年终身不娶——2015-10-21 04:20 重庆晨报

![该说不说,此招虽狠,但胜算极高[捂脸哭]](http://image.uczzd.cn/9819438455373776634.jpg?id=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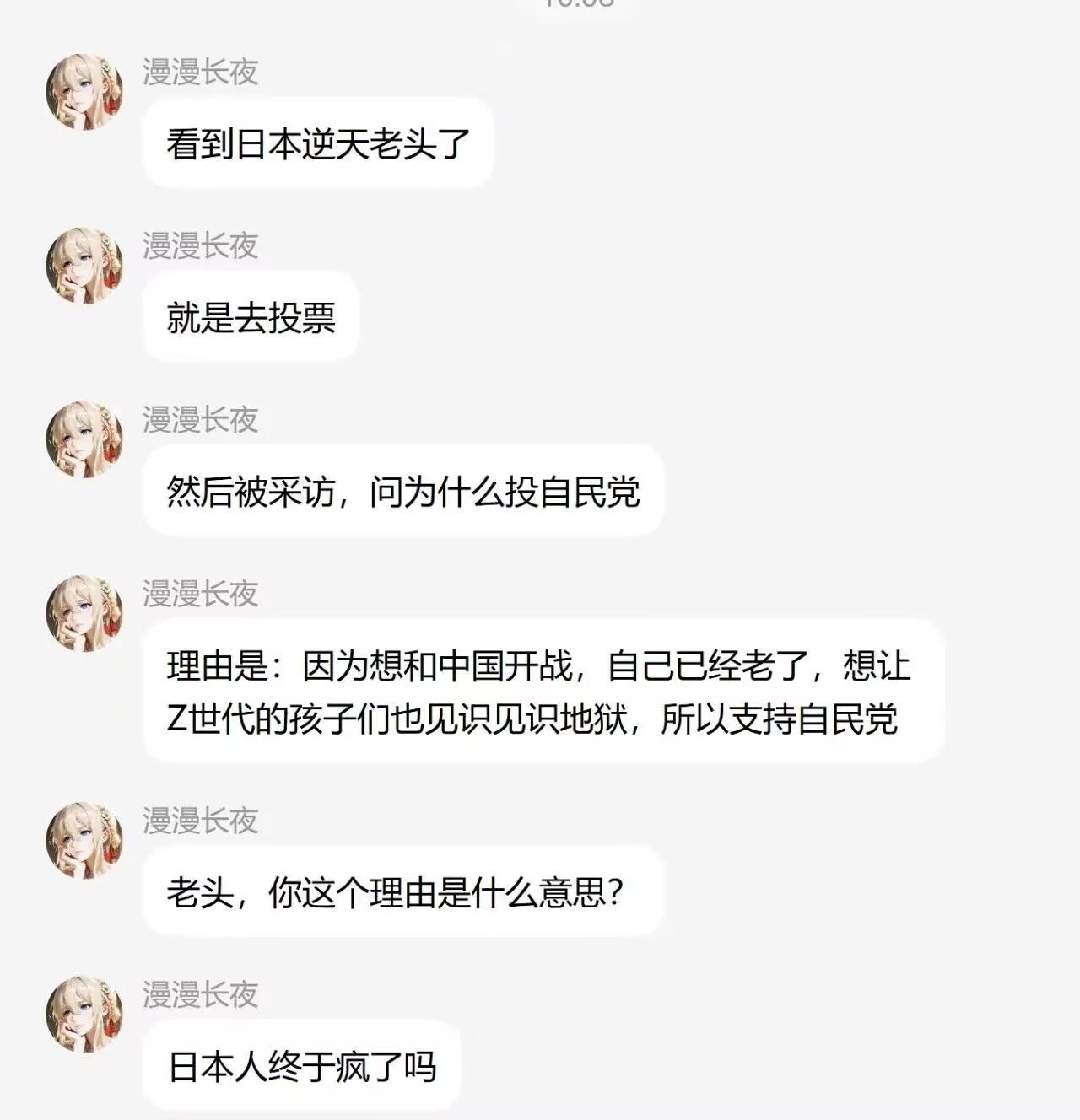
![话说太满直接翻车了[吃瓜]](http://image.uczzd.cn/17361602998108784539.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