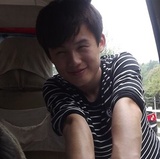诊室的门没关严,走廊里嘈杂的脚步声、叫号声全挤了进来。 男人往椅子里一靠,眉头拧成一团,眼神扫过医生的白大褂,又扫过桌上的病例本,最后停在墙角一个不起眼的污渍上。 他没先说自己哪儿不舒服,而是开了口,一口流利的中文,调子却飘在天上:“你们这儿,真是又脏又乱。” 医生手里转动的笔,停了。 男人没看医生,自顾自地继续说,像在宣布一个真理:“在美国,医院跟五星级酒店一样,哪有这么多人,哪有这么吵。” 他说话的时候,下巴微微抬着,嘴角撇着,仿佛空气里都漂浮着他闻不惯的味道。 整个诊室安静下来,连走廊的声音似乎都小了。医生把笔轻轻放在桌上,抬起头,目光平静地看着他。没说话,也没表情,就那么看着。 那眼神里没有愤怒,却比任何质问都重。 男人被看得有点不自在,清了下嗓子,把腿翘了起来,补了一句:“医生水平另说,就这环境,天差地别。” 这话一出,门口探头探脑等着叫号的几个人,默默把头缩了回去。 说白了,有些人的身体最老实,跨过太平洋,就为了这一张几块钱的挂号单。 可偏偏,嘴巴最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