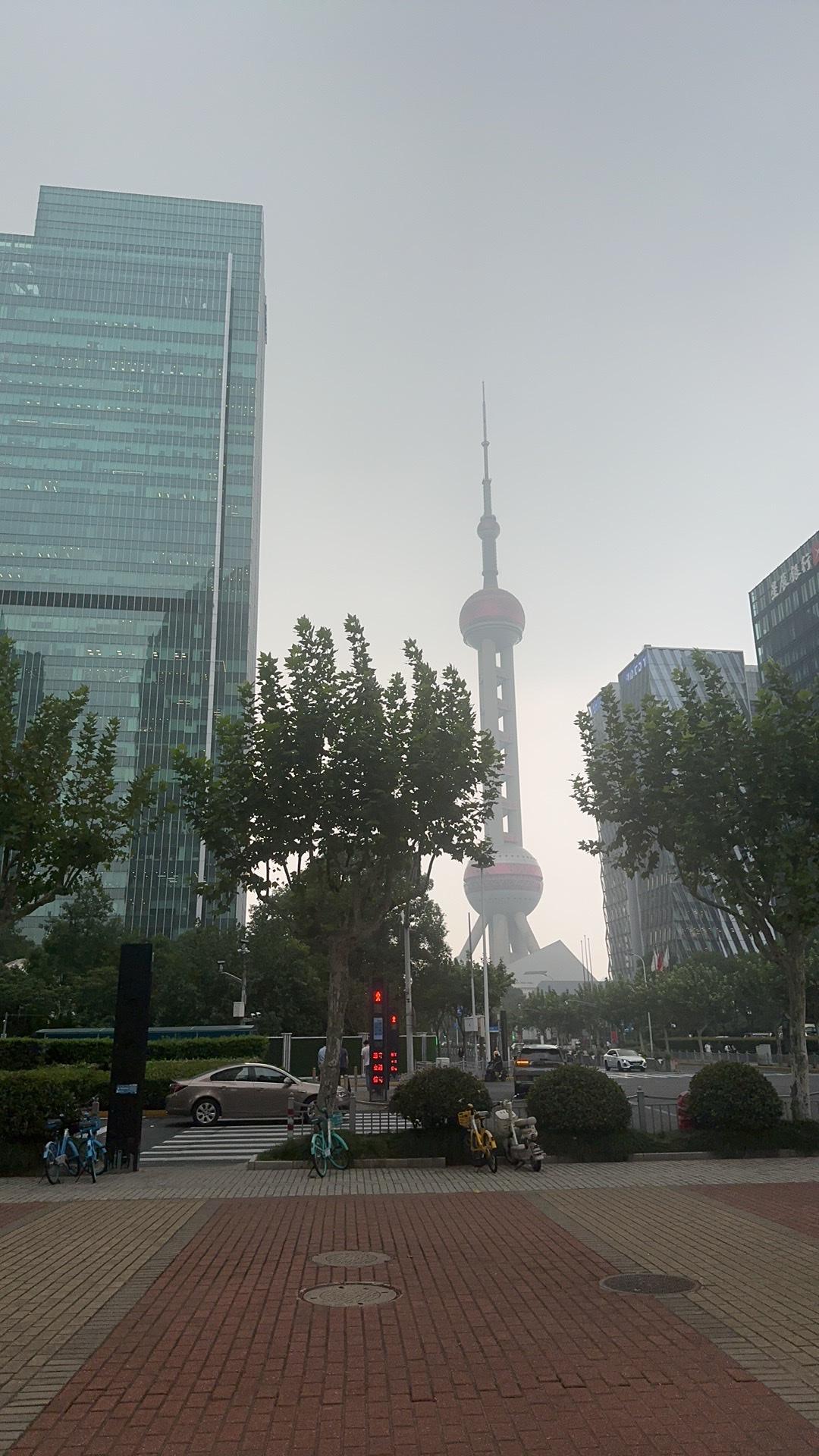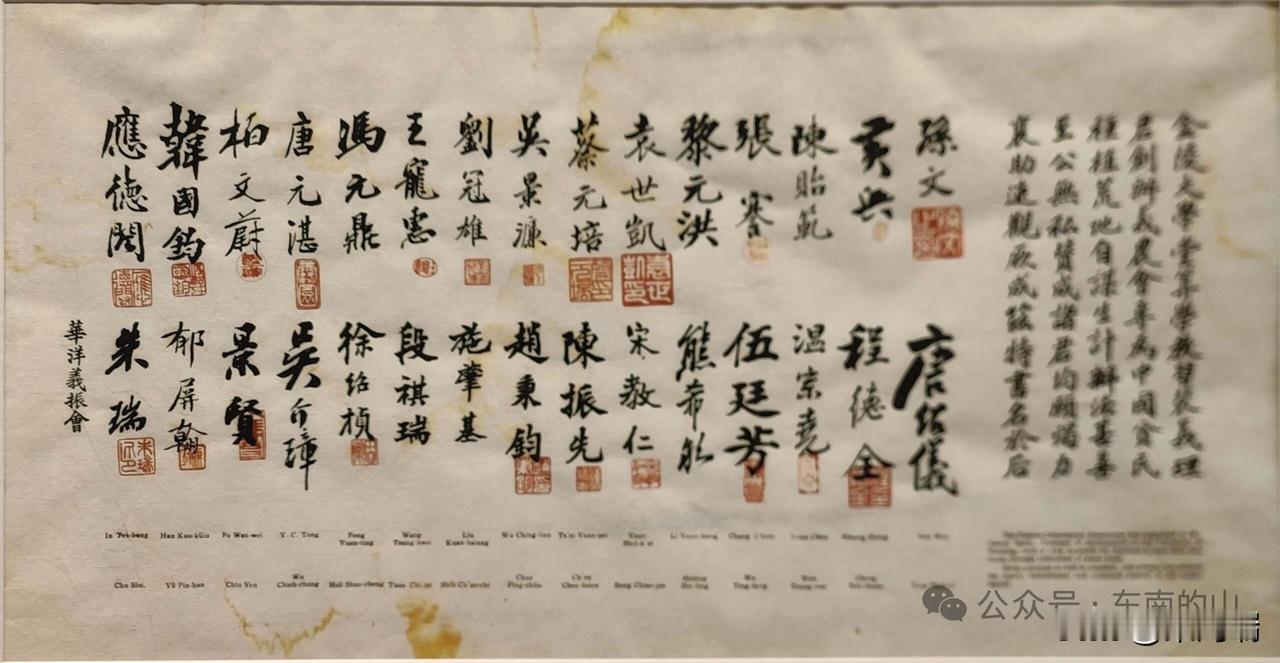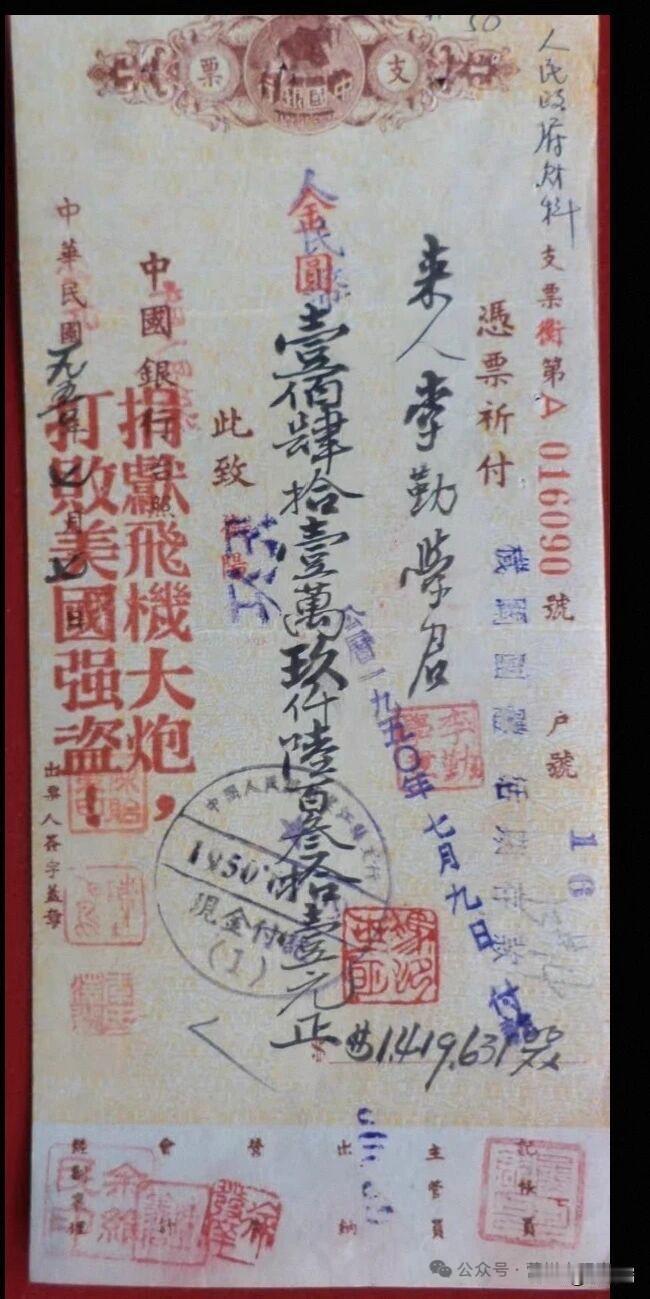1943年5月,因为掩护队友突围,便衣队队长师富昌被30多名日军包围。在这紧要关头师富昌捡起地上的土旮旯砸向日军,没想到日军全部被吓得匍匐在地上。 敌人卧倒的瞬间,师富昌已转身借着田埂滑进一片芦苇荡。子弹从头顶掠过,擦破胳膊,血流下来。他没有停,嘴里咬住布条,一边包扎伤口,一边往村东跑。他清楚,只有拉开距离,才能再拉回主动权。 三天前,冀中军区第四军分区接到命令,要将三名重伤干部送往安国后方医院。任务本由主力小队执行,但因道路封锁临时改由师富昌带队。 他熟悉蠡县至高阳一带的沟渠地形,靠一张民兵画的手绘图,领着人从暗渠走了一夜。返回途中,刚走出地道口就碰上日军巡逻队,伤员已转移,他选择把火力引开。 这不是他第一次独自断后。1937年蠡县沦陷时,他扛着祖传猎枪加入地方武装。那年冬天,他带两个队员夜袭据点,缴回的步枪成了全村唯一的制式武器。 后来编入冀中军区便衣队,他带出的队伍平均年龄不过20岁,多是猎人、农民出身,没有正规训练,但能用三四人炸毁一段铁路,能在白天混进敌人修的炮楼,晚上再点把火炸个干净。 突围那晚,他没直接回根据地,而是绕到大王庄附近,蹲守那股日军的驻地。他听村民说,那些兵临时驻扎在祠堂里,夜里换岗混乱。 他没有犹豫,写信让冀中游击小队准备协同作战。等第三天夜里,所有人就位,他亲自带头翻墙破门。打响五分钟后,祠堂陷入混乱,敌人从后墙逃窜,被伏击的民兵击毙。 缴获的三挺机枪被送往军区,还有步枪二十多支。可这一战没人知道,师富昌胳膊上的伤口裂开,伤口流了脓。他咬牙从村里走到高阳的后方医院,腿一软就昏在门口。 他从不主动讲这些,直到战后整理战报,队员才知道那天他没吃过一口饭。 他打仗不靠理论,靠的是经验和对日军心理的洞察。他清楚敌人怕突袭、怕地雷、怕不确定的威胁。他研究敌人夜里换岗节奏,观察步兵警戒角度,甚至会让队员伪装老农混进集市获取情报。 他也能预判敌人怕什么——那块土旮旯落地的沉闷声,在日军脑子里就是手榴弹的前奏。 《冀中抗日战争实录》里记载,便衣队平均每年出击近百次,任务多是突袭、爆破、缴粮、护送干部。冀中敌后战场极其艰苦,粮食靠群众供给,枪弹靠缴获,棉衣靠旧物缝补。 师富昌带队时,队员常年脚穿草鞋,冬季出动前他会把炒面分成一人一撮,用布包着挂在脖子上,实在饿得不行就嚼两口。 他不许乱杀伪军,每攻下一处据点,要先查明敌我身份;他也不许抢百姓一针一线,哪怕急缺物资,也要让队员挨家借。他说:“咱们是护这片地的人,不能自己砸锅。” 那年秋天,蠡县南庄的一位老太太,把她儿子的棉衣送给便衣队,说:“你们多撑一天,我们就多活一分平安。” 师富昌穿着那件补丁衣服,带人炸掉了日军在河西修的桥梁,切断一段铁路线整整九天。 那场“铁壁合围”行动后,日军在冀中多处据点加强封锁,便衣队的生存空间愈发狭小。但师富昌没退。他把队伍拆成三人小组,活动半径缩小,把“破坏”变成“骚扰”,把“打据点”变成“打点位”,让敌人始终摸不清方向。 1944年春,他在一次战斗中腿部中弹,仍坚持带队行动,直到根据地移交后方才返回治疗。他不是战功显赫的将军,却在敌后暗线上,守住了一道抗战生命线。 那块土旮旯砸出的,不是笑话,是敌人心里的恐惧,是敌后抗战的战术结晶,也是一个便衣队长在战场最被动时的破局。打仗靠枪,也靠胆,更靠对敌人心理的拿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