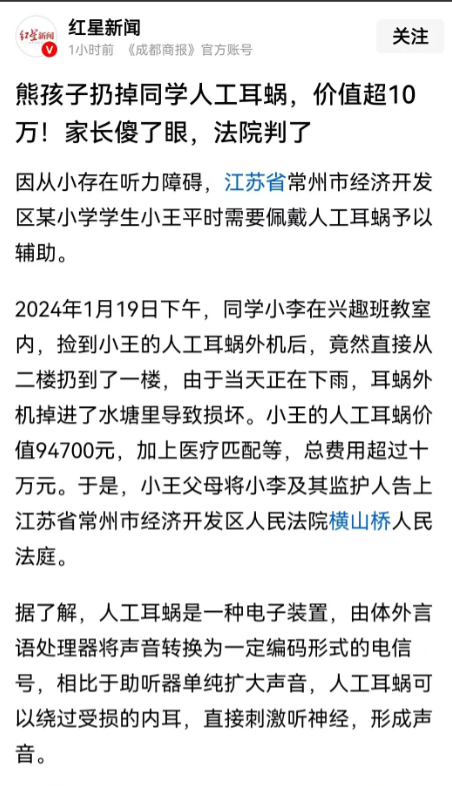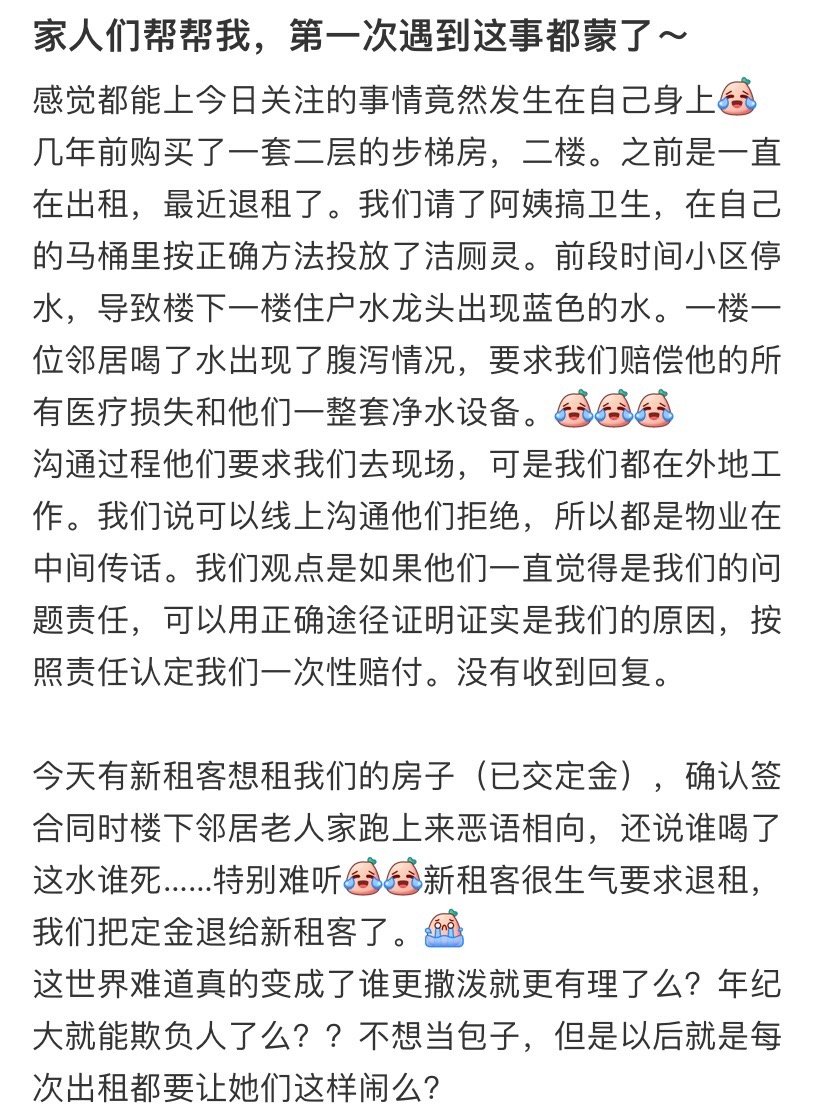吉林,近五旬货车司机因P娼被拘,却在拘留第5天突发脑干出血,历经230天抢救仍不治身亡。家属质疑:体检报告显示“高血压3级”却仍被收押,发病前关键2小时监控离奇消失,拘留所医疗配置形同虚设是否致命漏洞?家属将警方告上法庭,索赔154万元。经过审理,百万赔偿诉求却缩水至7万?真相背后,一场关于执法程序、生命权保障与赔偿边界的激烈博弈浮出水面——当公民在拘留所内遭遇不测,究竟谁该为生命买单?
(案例来源:裁判文书网)
2015年4月15日,时年49岁的货车司机沈某(化名)因在家中与冯某(化名)进行嫖娼交易被公安机关当场查获。
市公安局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于同年5月7日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0日并处罚款5000元的处罚决定。令人扼腕的是,这场看似普通的行政处罚最终演变成一场生命权争议的悲剧。
被拘第5天清晨7时30分,沈某在拘留所内突然抽搐呕吐。
同拘室人员发现异常后立即报告,值班民警迅速将其送往某医院抢救。诊断显示沈某突发脑干出血并破入脑室,次日转至市中心医院持续救治。
经过230天与死神的搏斗,沈某最终于2015年12月27日离世,医疗账单定格在41万余元。
据公安机关提交的证据显示,沈某被收押前曾在友谊医院进行体检,记录载明其患有"高血压3级(很高危)"。
这份由民警陪同完成的体检表成为认定沈某自身健康风险的关键证据。但家属质疑:若沈某确属高危患者,为何仍被收押?且体检报告未见患者本人签字确认,真实性存疑。
沈某之子坚持认为,父亲平素从事高强度运输工作,被拘时意识清醒、行动正常,根本不存在严重高血压病史。
更令其无法接受的是,拘留所未按规定配备医疗设施,且在沈某发病前两小时的监控录像神秘缺失。家属主张,正是这些管理漏洞导致未能及时发现病情征兆,最终酿成悲剧。
在庭审中,沈某家属索赔154万余元,提出如下主张:
第一,警方提供的体检报告真实性存疑,高血压认定缺乏依据。
第二,拘留所未配备必要医疗设施,违反《拘留所条例》。
第三,关键时段监控缺失,应推定管理存在重大过失。
警方则不认可,抗辩称:
第一,行政处罚程序合法、量罚适当。
第二,及时送医尽到救治义务,死亡属意外事件。
第三,已垫付46万余元医疗护理费用。
那么,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1、行政拘留合法性的双重审查
在实体层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六十六条对嫖娼行为的处罚要求以“金钱交易”为核心要件。
本案中,公安机关需证明沈某与冯某存在实质交易行为,包括现金交付记录、双方陈述一致性等直接证据。若仅凭现场抓获的单一证人证言,未提取转账记录或扣押嫖资,则证据链存在瑕疵。
在程序层面,《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规定,作出处罚前应告知当事人事实、理由及申辩权。
案卷材料若未体现处罚前的权利义务告知记录,或存在程序违法风险。值得关注的是,沈某在收押时体检表记载“高血压3级”,根据《拘留所条例》第十九条,此类高危患者应建议停止拘留,但公安机关仍继续执行拘留,此程序选择是否合规,直接影响处罚行为的整体合法性。
2、因果关系的“多因一果”判定
沈某死亡与拘留行为的因果关系需运用“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分析。
在医学层面,脑干出血多为长期高血压引发的自发性疾病,拘留期间的紧张情绪可能成为诱因,但非直接致病因素。
在法律层面,需判断行政机关的不作为是否显著增加死亡风险:其一,拘留所未配备基础医疗设备,导致无法对高血压患者进行日常监测;其二,发病时若因监控缺失延误救治,则管理缺陷与结果存在关联性。
值得注意的是,沈某在转院后存活230天,说明及时送医避免了即时死亡,但长期治疗产生的巨额费用是否属于可赔偿范围,需结合《国家赔偿法》中“直接损失”原则,判断医疗费与行政行为的关联程度。
3、赔偿责任的比例划分逻辑
本案,法院之所以认定警方承担30%的责任比例,蕴含三层裁量逻辑:首先,过错比重衡量,行政机关的管理瑕疵属次要原因,相较于疾病主导性(70%),划定30%体现过错与结果的原因力配比;
其次,风险分担原则,行政机关对特殊体质被拘留人负有更高注意义务,未履行该义务即应承担相应风险;
最后,损益平衡考量,全额赔偿可能过度加重公共财政负担,而象征性赔偿又不足以警示行政机关,30%的比例在个案公正与执法效能间取得平衡。
此外,法院还支持了家属主张的精神抚慰金,单独计付5万元,突破《国家赔偿法》第三十五条“造成严重后果”的抽象标准,体现法院对长期救治过程中家属精神痛苦的特别关注。
最终,法院支持了沈某家属约7万元赔偿金额,以及支付5万元精神抚慰金,驳回了其他诉求。
对此,大家怎么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