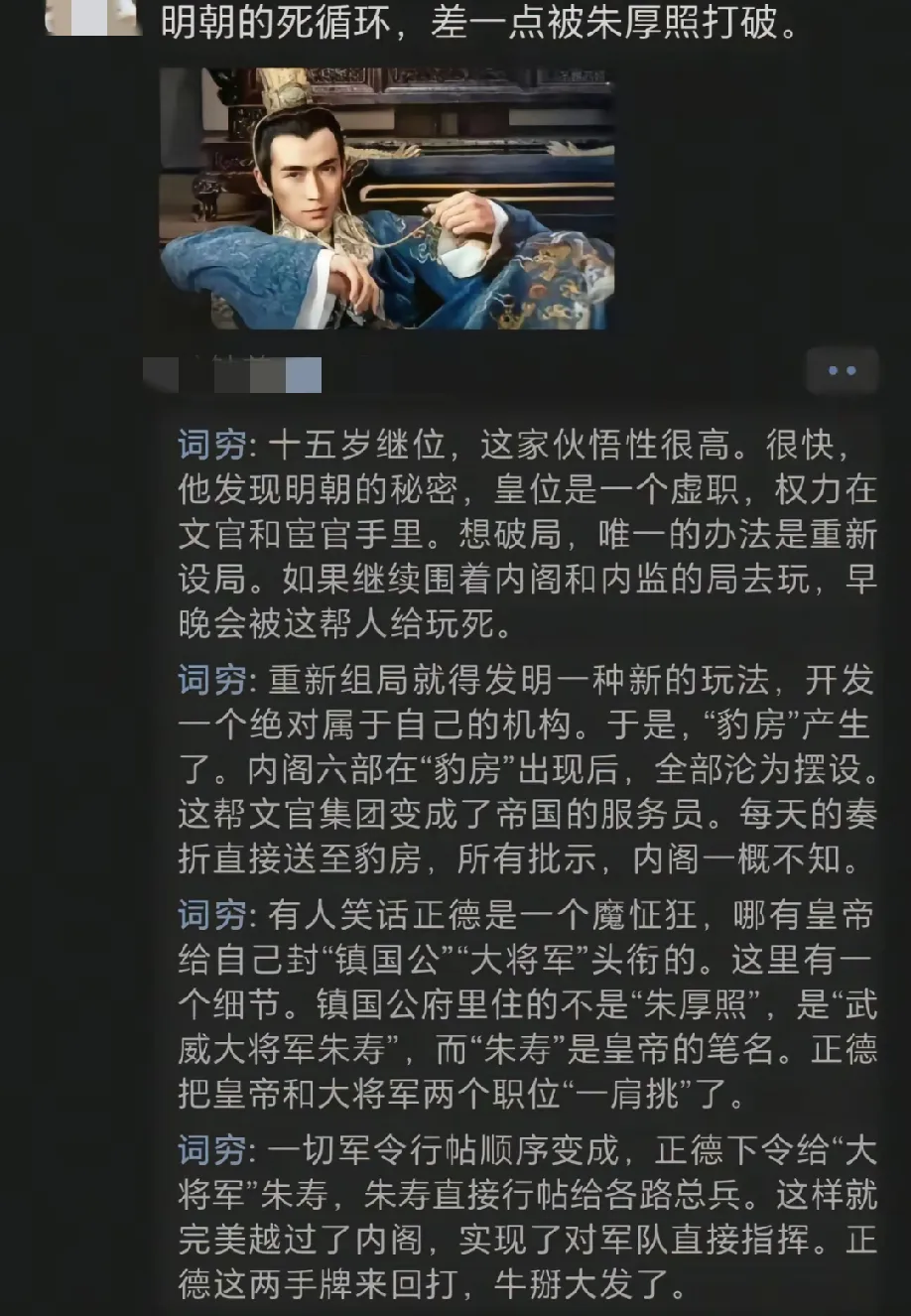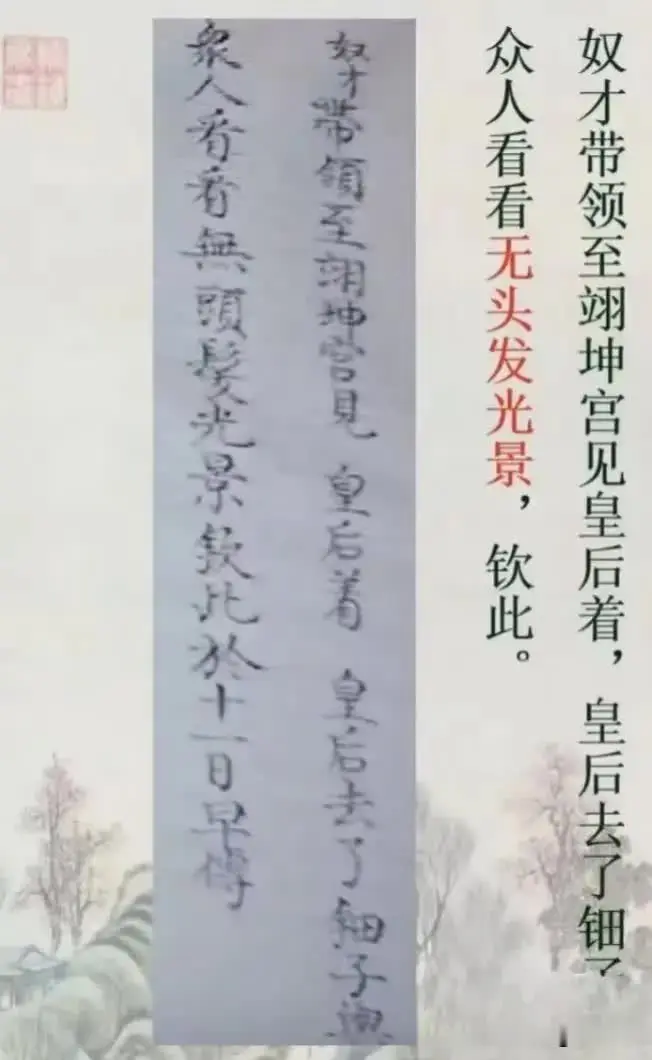公元757年,年过古稀的太上皇李隆基在六百名侍卫的护送下回到了长安,新帝李亨带了三千精锐前来迎接。见李亨这阵势,李隆基赶忙让侍卫们丢开刀剑投降,他勉强笑着说:“我只是想回宫安度晚年。”这话说完,二人便打算迈步进宫,可谁走在前面呢?父子二人又僵持住了,只能尴尬地问群臣,可大臣们也支支吾吾,没人敢回答。 至德二年(756年),李亨成功收复长安,准备迎接其父唐玄宗从四川返回。在他们间的书信交流中,虽表面客气,实则各藏心机。尽管李亨的态度令唐玄宗忧心,但长安一旦收复,唐玄宗作为前皇帝也无法继续在四川逗留。因此,他带着复杂的心情踏上了返回长安的路途。 唐玄宗逃往四川时的旅途充满艰难困苦,风餐露宿,常受人白眼。而此次返程虽然道路较为顺利,但在扶风的接应却遭遇了儿子李亨的计谋。李亨以孝顺之名派遣迎接队伍,实则另有所图。当唐玄宗与迎接的军队在扶风相遇时,情形突变。 唐玄宗身边有600名禁军护卫,而李亨却派出了3000名全副武装的精兵。这些精兵并未向唐玄宗及其护卫队表现出尊敬或礼貌,反而直接将600名禁军的武器缴获。缴械完成后,3000精兵的首领宣布,太上皇的保护将由他们接手,而原来的禁军可以自行离去。 玄宗不禁自嘲地说道:“现在已经到了大唐的安全地界,还需要将士们保护我吗?”这是对自己命运的讽刺,也是对现实的无奈妥协。 这一行动明显不仅仅是迎接,更像是一种武力解除和押送。面对这样的局面,唐玄宗深感无力,因为自己已不再是国家的统治者。他意识到,尽管身为太上皇,实际上已被完全边缘化,只能顺从儿子的安排,继续他的归途,回到了名义上尊贵却实际无权的长安。 几天后,唐玄宗抵达咸阳,此地已有他的儿子,即唐肃宗李亨,恭候多时。在咸阳望贤宫的南楼,一幕感人的父子重逢上演。唐肃宗脱下象征皇权的黄袍,换上象征臣子的紫袍,向楼上的玄宗行拜舞礼,展示对父亲的尊重和欢迎。 见到儿子,玄宗情不自禁跑下楼来,与李亨相拥而泣。李亨也被父亲的悲痛所感动,跪地抱住父亲的脚,同泣。情绪稍定后,玄宗试图将黄袍披在李亨身上,意图让其回归太子之位。然而,李亨坚决推辞,认为玄宗仍应继续执掌帝位。 此时的对话充满了戏剧性,玄宗指出李亨击退安禄山,收复长安的功劳,强调皇帝之位理应属于李亨。经过这番仪式性的表达后,李亨终穿上黄袍,正式确认了他的皇帝身份。这一切虽带有演戏的成分,却也反映了权力交接的复杂情感与历史责任。 在咸阳的次日,随着长安之行的临近,李亨为表现孝顺之情,亲自扶持唐玄宗上马。他不仅亲自为父牵马,还特意骑到前方左侧,继续展示他的恭敬和尽职,似乎在不断地演绎一场完美的孝道表演。 这一幕被《资治通鉴》的记载所捕捉,唐玄宗见儿子表现出如此的恭顺,向身边的随从表达了他的感受,他说:“吾为天子五十年,未为贵,今为天子父,乃贵耳。”这句话反映了他对当前地位的一种复杂感受——作为皇帝五十年,他从未感到真正的尊贵,而作为皇帝的父亲,他感受到了一种不同的“尊贵”。 然而,对于这种表述,《资治通鉴》中的元朝注解者持批评态度,认为唐玄宗应当对失国之责有更深的自我反省,而不是在随从面前夸耀自己作为天子之父的尊贵。注解者直言:“玄宗失国得返,宜痛自刻责以谢天下,乃以为天子父之贵夸左右,是全无心肠矣。” 这位元朝的学者的批评可能未能完全体会到唐玄宗当时的处境。作为太上皇,他已无实权,处于被动和依赖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唐玄宗的言论也许不仅是对现实的一种无奈妥协,更是一种生存策略。在权力的边缘游走,他需要表现出一种满足和无害的姿态,这不仅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余生,更是为了在复杂的宫廷政治中保持一定的尊严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