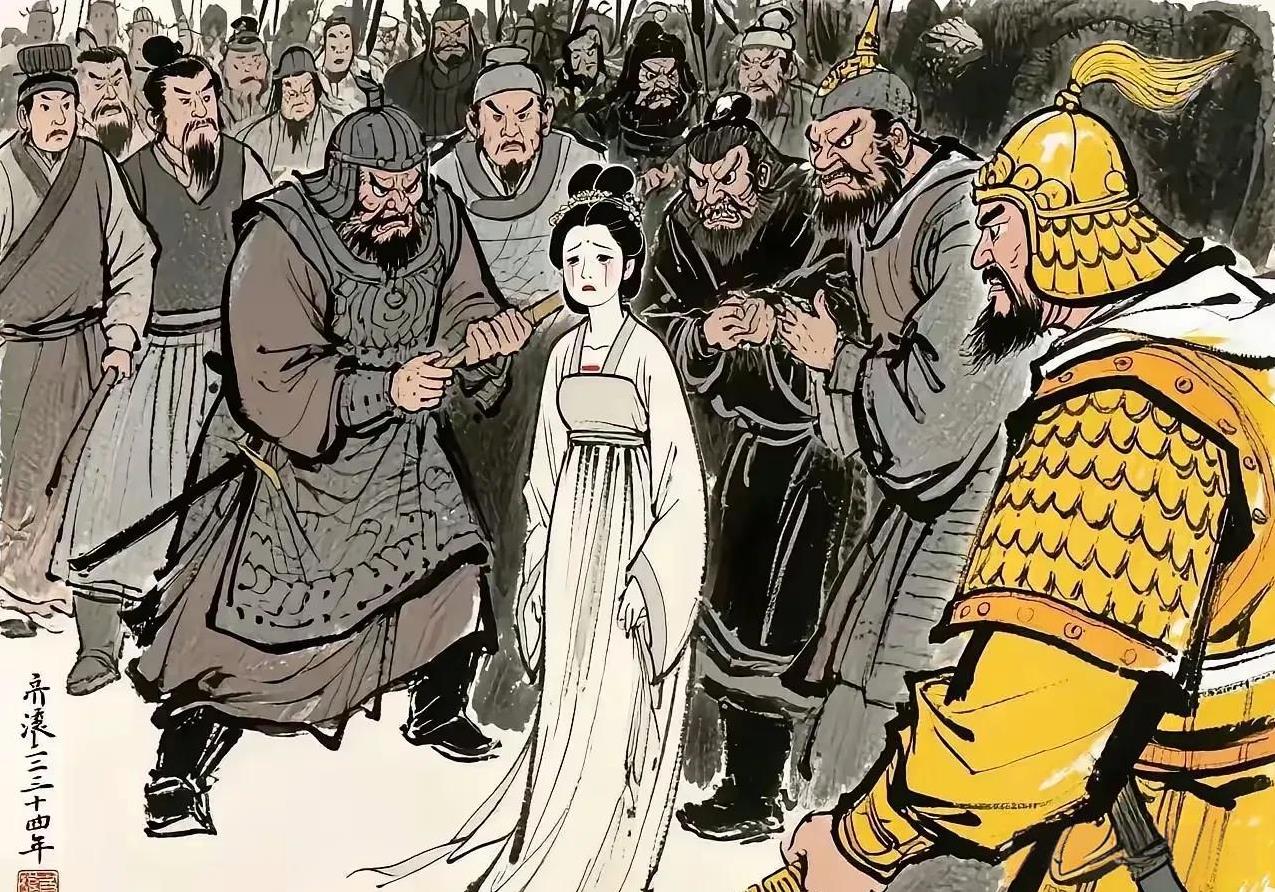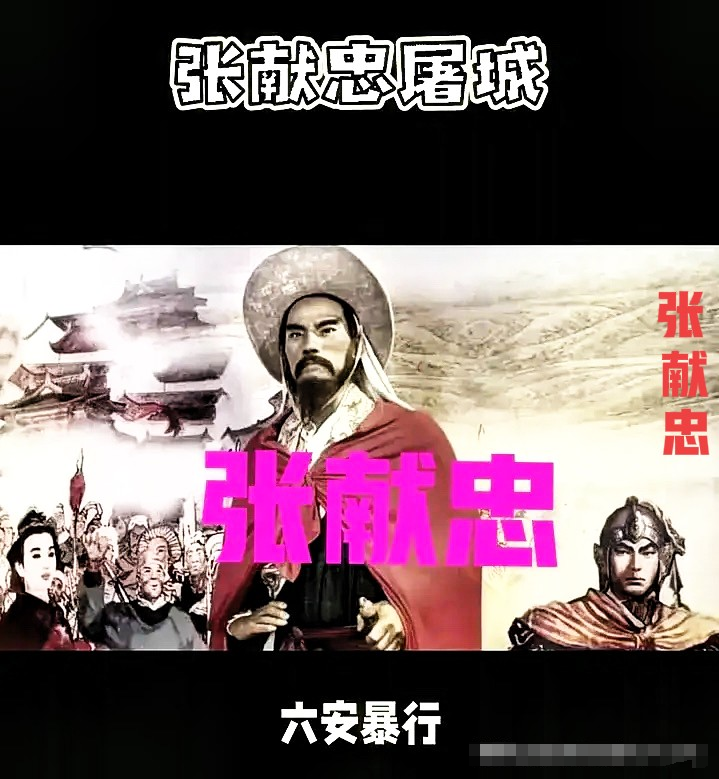牛舌被割,牛还活着。农夫扯着缰绳站在县衙前,嘴唇发抖,不敢再往前迈半步。他不是来讨公道的,他是怕,怕牛活不成、自己反被治罪。可站在案桌前的那个人没说一个废话,只让他回去杀牛、卖肉,说人自然会来。第二天,果然,一场告状掀翻旧账,贼人自己跳进了局里。
包拯进仕,是景祐年间的事。那年他三十多岁,中了进士,却没有立刻入朝。别人高头大马奔仕途,他却回了老家,守孝十年。这十年,他不说一句笑话,不见外人,衣食简陋,一步不出祖宅。 朝廷看重这份坚守,等他守孝完毕,直接安排他去了天长——一个在江淮之间的小县。包拯当上县令时,已年近四十,正值中年,不再年轻。他到了任上,没有声张,没有拜访,连轿都不坐,步行穿街走巷,踏查民情。
他不敲锣打鼓,也不盯政绩。他盯的是县里的弊案,百姓的呼声。朝中人评价他“清而不傲、明而不浮”。老百姓更直白,说这人是“黑脸青天”,不是好惹的主。
在天长,他接过的案不多,审结的却一个比一个狠。有户人家三年不交赋税,原因是县吏中饱私囊,他亲自查账,把贪官押送开封。有次有人告状田界被侵,他带人下地丈量,半日清楚,判得服服帖帖。
县里风气慢慢变了。连集市的小贩都说,别惹事,有事别怕,有个包青天在。
这才是故事发生的背景:天长百姓信他,小民敢说话,才有了后来这桩“牛舌案”。
那天早晨,天还没亮透,县衙外就来了个农夫。他满脸是汗,身后牵着一头耕牛,牛喘得粗,脖子上挂着血,嘴里流着黏稠的浆水。
牛的舌头,被人割了。
这事说起来简单,可在宋代,这是大事。牛是耕作的主力,是朝廷重点保护的牲畜。民间私宰耕牛,是重罪,不管是病死还是老死,想杀都得官府批准。
农夫吓坏了。他不敢杀牛,又不敢不杀。牛没舌头,吃不了草,活不过三天。真要死了,按律法,他还得担责。
所以他不等牛死,就拖着牛来报官。他不是为了破案,是想撇清责任,保住自己这条命。
包拯听完,没有动声色。他知道事没那么简单。
牛不是乱走的东西,割舌不是顺手为之。下手的,必然有因。
他没多说,只让农夫把牛牵回去,宰了。然后把肉带到集市去卖。
没给解释,也没多问。农夫愣住了,但最后照办。
这个决定,看似草率,其实藏着一整套布局。
农夫回家后,越想越不踏实。他怕,一怕犯禁,二怕惹祸。但他也明白,包县令不是乱说话的人。
当天晚上,他找来屠户,按规矩处理了那头牛。
牛很快被宰,肉切成大块,装上箩筐。第二天一早,他照吩咐去了集市,摆摊卖肉。
肉是热的,颜色鲜亮,吸引了不少人。可没过多久,人群中冒出一个人,眼尖嘴快。
他看了几眼肉,又盯着农夫,突然转身跑去县衙,举报了。
说是:某人在街头私宰耕牛,违法!
这一幕,正中包拯下怀。他等的不是肉摊,也不是谁吃牛肉。他等的,就是这个举报的人。
这个人,一看就不正常。他怎么知道那头牛是耕牛?又怎么知道是昨天割舌、今天宰杀?
没人通知他,也没目击者。可他来得那么快,认得那么清楚。
这不是巧合,这是心虚。
举报人一进衙门,包拯便让他讲来龙去脉。他说得倒利索,说是昨天就见农夫把牛拉进院子,今天又在市场上看到卖肉,于是怀疑是耕牛。
可包拯看着他,什么都没说。
他看人,不看话。
这人眼神闪躲,说话急促。更重要的是,他说的时间线对不上。昨晚,牛还没死。他怎么知道今天这牛肉,是那头耕牛?
越问越乱,越问越慌。最后,那人崩了。
他低头承认,是他干的。因为和农夫有过节,想让他吃官司,才割了牛舌。料定农夫不敢宰牛,只能干等死牛,或是违法私宰。
没想到,包拯早看透这心思,故意让农夫宰牛卖肉,逼他出面举报。
他跳出来,不是告状,是自投罗网。
案情明了,处理也快。包拯没有拖沓,定罪、行杖、赔偿,一样不少。
这起案子,县衙没惊堂木,也没传唤人证,全靠一计“设局”。
后来人说,包拯断案如神,是神探。这案子却说明,他更像猎人。设下圈套,放出诱饵,猎物自己钻了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