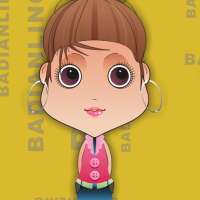1979年妻子因为李伯清穷而离婚,小儿子判给了前妻,大儿子跟了他。 李伯清这个人啊,真是典型的“命里带苦也带戏”的角色。 从出生开始,他就像是被命运往生活底层狠狠地摁了一把。 1947年,成都,战后初年,百废待兴,李伯清一落地就赶上了这个混乱时代。 家里原本是中医世家,按理说有点文化、有点传承,可惜天不遂人愿,他才四岁,父亲就走了。 母亲后来改嫁,李伯清也跟着改了姓,从“陈”变成了“李”,这一变,也像是把原本的命改了个方向。 他读完小学就辍了学。 不是不想读,也不是读不起学费,而是连拍一张准考证用的黑白照片都没钱,这才算真正懂得什么叫“穷”。 十几岁开始,他干过装卸工、拉架子、卖小商品,甚至连蹬三轮车也干过。 那时候他最羡慕的三种职业,司机、炊事员、三轮车夫,全都不是因为有多体面,而是能挣到现钱,不拖不欠,饿不死人。 日子再苦,嘴上得有活气。 他就是那种一边啃冷馒头、一边还能讲段子哄大爷大妈笑的人。 这嘴皮子,是从小练出来的,也是生活逼出来的。 那会儿街头巷尾没什么娱乐,大人们围在一起聊天打牌,他就在旁边听,也在旁边插。成都人说话本来就有股子味儿,他一说,别的娃儿就都不吭声了。 1970年,他结婚了。 娶的是一个北方下来的知青姑娘,两人结婚后很快有了两个儿子。 那时候家里日子紧,两口子拌嘴也多。 到1979年,这段婚姻就散了,李伯清自己总结,说是“穷”是第一大杀手,再就是脾气大,说话冲。 年轻时他当厨师,有一次因为临时工没电影票看,当场就甩锅不干了。 家里有个男人这么爆脾气,女人哪撑得住?离婚后,大儿子跟了他,小儿子归了前妻,就像抓阄一样,谁也没得挑。 那一年他32岁,没工作没名声,一个三轮车夫,带着儿子住简陋平房。 白天蹬三轮,晚上偶尔去茶馆歇脚。 就是在这样一个看似平淡又灰头土脸的日子里,他的命运忽然就转了弯。 有一次他蹬完三轮车口渴得不行,走进文殊院附近一个茶馆要了杯茶。 正好里面几个人在聊武松——是那种民间最常见的闲谈,有人说武松侠义,有人说他能打。 李伯清听着听着,一时嘴痒就插话,说:“武松厉害个啥子嘛,仁义不如宋江,武艺不如西门庆,气力也不如蒋门神。”这一出口,全场先愣后笑。 凑巧茶馆里正坐着两个老说书艺人,一听这小子嘴皮子利索,起哄让他上台讲讲。 他哪里真的会说评书?只好说:“那我就给大家讲个故事嘛。”结果讲着讲着,就讲出味来了。 那天讲完,有人往茶几上一摞零钱,加起来两块多,朋友还帮他收起来。 他自己一个人站在门口,看着这两块钱,突然就眼泪下来了。不是感动,是觉得自己一张嘴,原来也能混口饭吃。 之后,他就真踏上了这条说书的路。 茶馆的茶铺老板开始给他安排下午场演出,一天讲两场,分成按人头收。 后来,他正式拜入成都评书名家周少稷门下,算是“入行”。 不过传统评书那套“开篇起、起承转合、落尾闭”的手法,他并不拿手。 他讲的东西很接地气,讲的是打工的糗事、街坊的怪事、机关里的笑话——不拿历史人物说事,直接拿自己和周围人开刀。 这种风格,后来他自己起名叫“散打评书”。 不像传统评书那样一本正经,而是“口语流”,笑料快节奏,段子接地气,用词也不讲究,骂骂咧咧全是市井话。 有段时间,街头的随身听里放的不是歌,是李伯清的段子。 成都年轻人走在街上听他说段子,还会学着他的语气说话。 1994年,他火了。 那一年,他的作品《徐洪刚热血颂》传遍四川城乡。 有人说李伯清是“巴蜀一张嘴”,有人说他是“人民的嘴替”。听众喜欢他,因为他不拐弯抹角,不装腔作势,说话带刺又带笑。 他骂人也骂得让人乐,吐槽也吐得有理,哪怕你今天被他调侃了,明天还想来听。 他真正厉害的地方在于,把川味儿讲进了现代人的骨头里。 他说:“以前我吃两块钱的烟,现在吃二十块钱一包的。”这是调侃,但也是事实。他从三轮车夫混成笑星,用的全是一张嘴,没靠后台,没走捷径。 他甚至没进体制,也没上春晚,却在四川成为街头巷尾的文化现象。 说起来也奇怪,他名声越大,人却越低调。 1995年,他悄悄皈依了佛门。别人出名了忙着投资、代言、捞钱,他去寺庙礼佛,成了四川佛教协会的副秘书长。 他始终觉得名利不是长久之计,嘴上的风光,终究要归于平静。 2007年,他剃度出家,在崇州的三昧禅林接受了仪式。 那天跟着他一起去的,有三十多个徒弟,气氛庄严得像过年。有人说他是不是跟妻子闹掰了,才跑去当和尚。其实不是。 他的第二任妻子徐茂,一直在他身边。 徐茂是成都本地人,出身知识分子家庭,比李伯清小了十几岁。 两人1998年结婚,感情一直挺好,李伯清虽然名气大,却从来没传出过什么绯闻。 他退休后不怎么出门,就跟她一起养花养狗、喝茶聊天。 后来他还搞了一个“皇家贝里斯”足球队,说是要给成都人搞点健康娱乐。 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喜欢诗,也喜欢狗。”就这么一句话,搞得大家哭笑不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