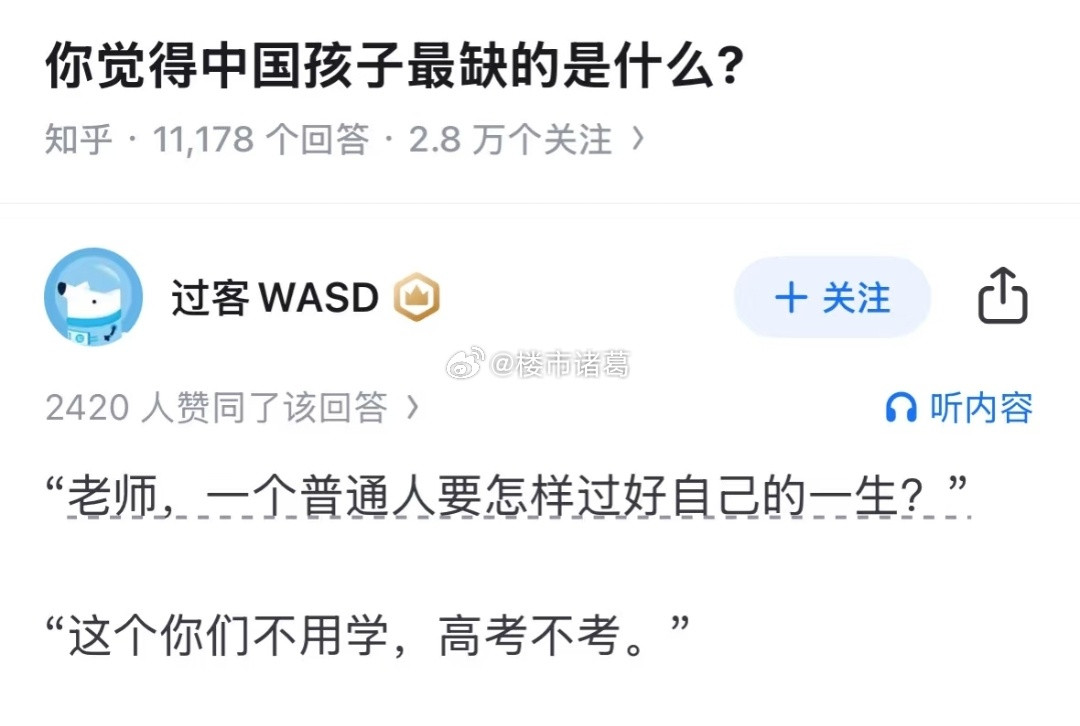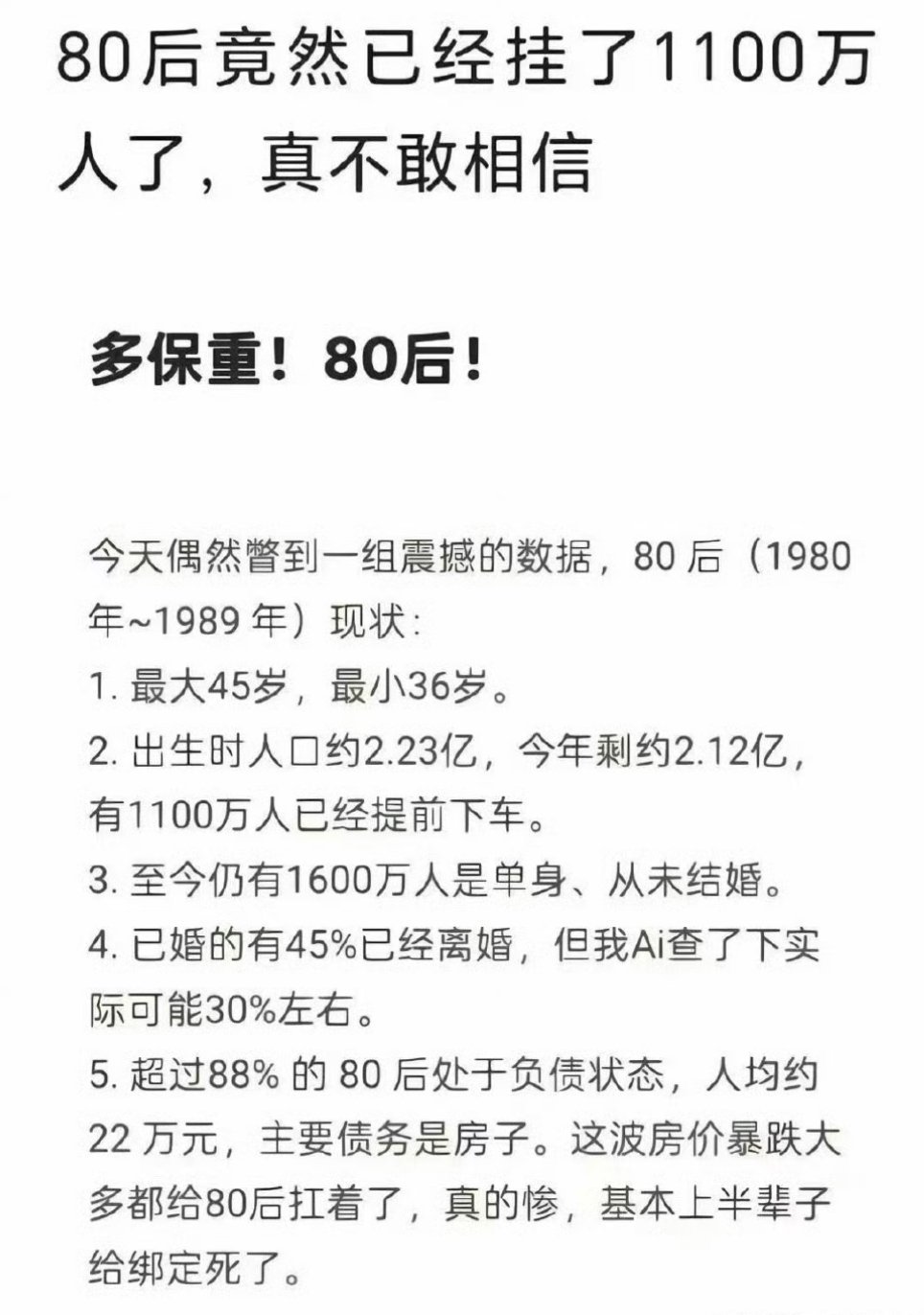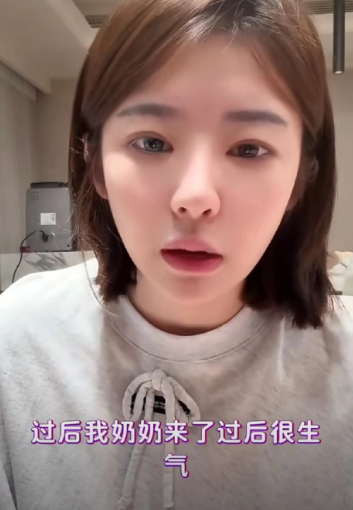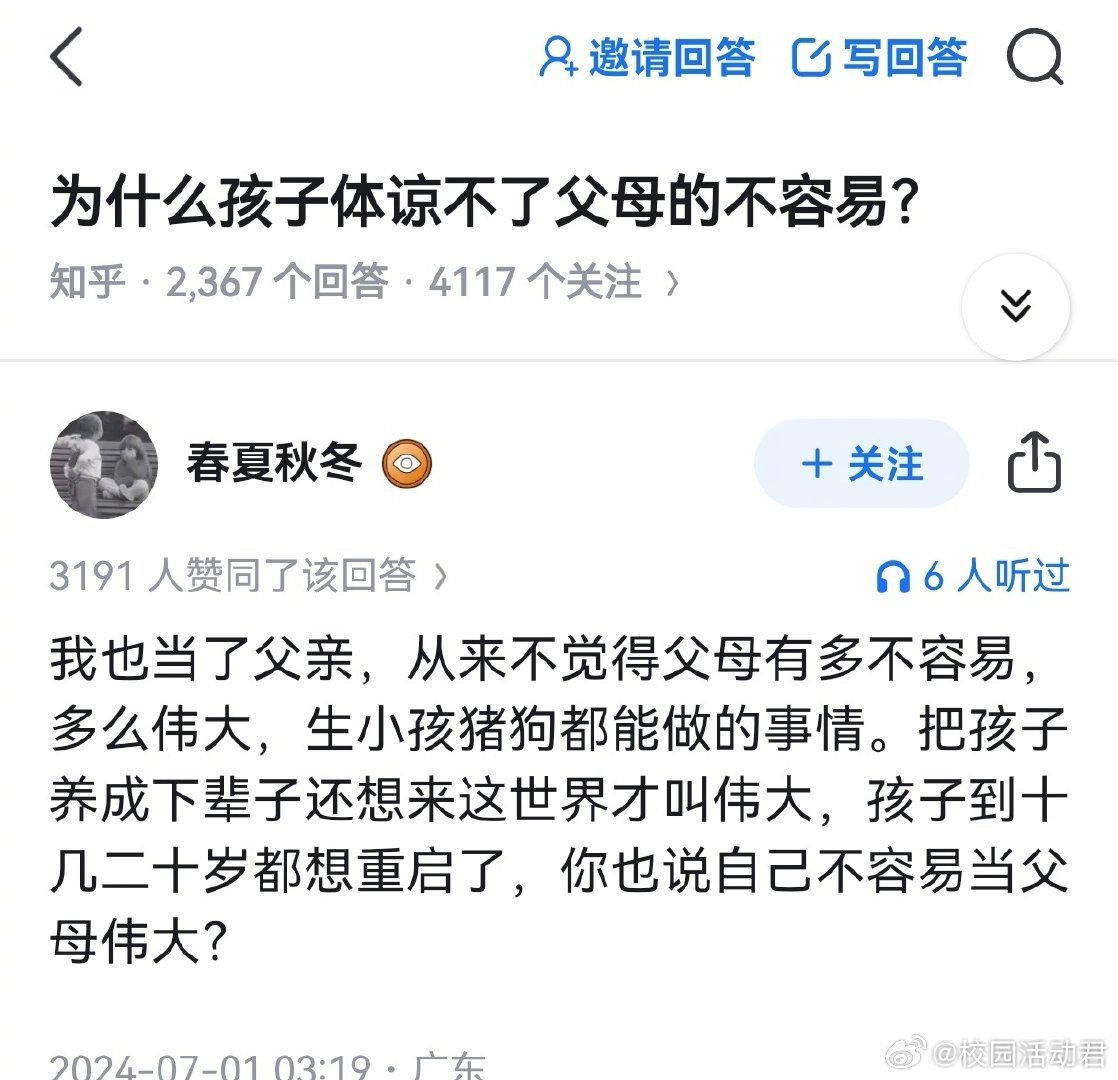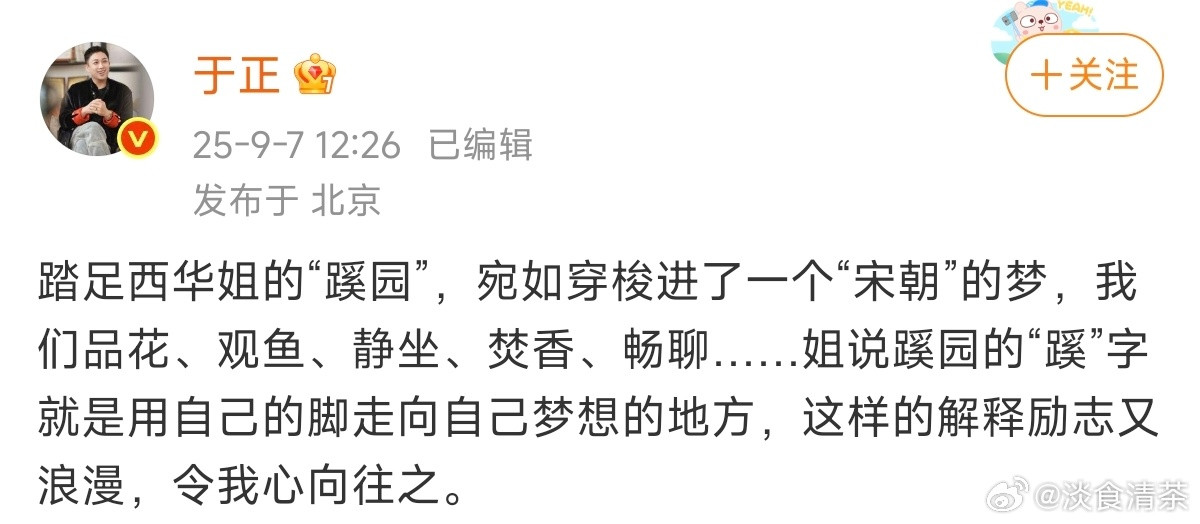1927年,李大钊英勇就义,三个孩子在一起,16岁的李星华,8岁的李炎华,4岁的李光华,同框合影,永恒的回忆! 那张照片是1927年的,三个孩子站在一起,站得挺直。 大的是李星华,十六岁,穿着暗色布衫,小辫盘得紧。中间那个是李炎华,才八岁,低头看地,像刚哭过。最小的,是李光华,四岁,小脸憋着,一只手揪着姐姐的袖子。 他们的父亲,李大钊,已经不在了。 照片照下来的时候,他刚刚被绞死没几天。 四月二十八号,行刑那天,天阴沉着,西交民巷那边封了路,刑场设在一片空地,草地都没来得及拔。 架子是新搭的,粗木横梁,铁钩挂在正中。 行刑官是北洋政府那边指派的,说不上名字。 他先喊了几句,没人理,李大钊也没动。他是第一个被挂的,走得稳,走到绳子下的时候停了几秒,好像在看天。 那天没太阳,天色跟锅底一样暗。 没有喊,也没有挣,过了一会儿,绳子收紧,人吊了起来。 四十来秒,没动静了。 那会儿他三十八岁。 人死得静。可这个人,不该是静的。你说他在北大讲课的时候,哪一次不是把手拍在讲桌上说:“我们不是读书人,我们是要翻身的人!”下面学生一哄而上,抄起笔记本开始记。有的没带纸,他就笑着把自己讲稿撕了递过去。 谁也没想到,走得这么快。 他是河北乐亭人,家里做小生意。小时候爱读书,祖父宠着,十几岁就许了亲,娶了赵纫兰,一个农村姑娘。两人感情不热不冷,但稳。他后来留学去了日本,纫兰留在家,把家里撑着。养孩子、种地、借钱送学费,全她一人。 他在东京,读书之外最喜欢的事是写传单。尤其是1915年那年,日本给中国下了“二十一条”,他气得不行,整宿不睡,写了《警告全国父老书》,印了一百多份,跑去散发。他说:“这不是读书,这是活命。” 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做图书馆主任,那年是1916。他头发梳得一丝不乱,穿长衫,笑的时候嘴角一边翘。人不高,站着讲课的时候,常常两只手插在袖子里。学生爱听他讲,尤其是讲俄国、讲十月革命。 他说:“革命不是喊口号,是改命。” 1918、1919那几年,他文章写得密,一篇接一篇。《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是干巴巴的话,却能看得人心里起火。 你要说他文采,不是写得华丽,而是像在跟你掏心窝子。 他把“庶民”这词写得重,他说咱们国家不是没希望,是没被这些人真正管过。 他组织北京的共产主义小组,自己是书记。 那些年他住回回营三号,一边教书,一边革命,一边教孩子。 家里日子紧巴,赵纫兰做豆腐、卖针线补贴,李大钊的工资一大半拿去救济党内同志。 有人问她苦不苦,她摇头,说:“这家不是我的,是这个国家的。” 后来情况越变越坏,1926年,张作霖的兵进北京,逮人、封楼、封报。李大钊没躲,每天照样上课、写东西、接头。他说:“我走了,别人怎么办。” 四月六号早晨,奉系军警突袭了俄国兵营。 李大钊在那里避风头,被抓了个正着。 传说当时他手里正翻着一本《资本论》,看了一眼,把书放下,自己站起来。他说:“不必推我,我自己走。” 押去西交民巷的路上,有学生认出他,远远地喊了一声“李先生!”他没有回头,只是把头微微点了点。 他在看守所里写了三份《自述》,有人说是交代,也有人说是给后人留的。 字写得密,每页都改过,墨迹晕在纸上。每段结尾都写“我不悔”。最后一页签名后,他加了一句小字:“为真理而死,虽死犹荣。” 他死了以后,家就散了。 赵纫兰抱着孩子们从北城搬到南边,又搬到通州。她身体不好,一病不起。1933年冬天,临终前吩咐李星华照顾弟弟,说:“不求你们出人头地,只别走歪了。” 五个孩子,各走各路。李葆华去了日本,读书、入党、回国、抗战、解放,最后做到副国级。别人问他有没有遗憾,他说:“我没爹的时候才十八,我知道怎么过。” 李星华是教师,在延安、在北平、在北京,一直教书,教到头发花白。她收集民间故事,出了一本《北方乡语小集》。扉页上写了一句话:“父亲说,话要讲给人听。” 李炎华流落多年,在乡下教过小学,后来进冀东建国学院。她从不提过往,办公室里挂的不是父亲遗像,是一幅写有“勤俭”二字的横匾。 李光华,那个站在照片最右边的小孩,后来当了工人、干了行政、进了中科院,做书记。人到老了还是喜欢喝一口,喝多了会说:“我娘走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怎么烧水。” 李欣华,最小的那个,从没见过父亲。他在北京做过校长,死在九十年代。学生给他立碑,碑上只写了七个字:“校长人好,话不多。” 家人从来没在公开场合合过影。 除了那一张,1927年的照片。站姿生硬,神情怯懦,衣角有褶,光线偏暗。那天照相的师傅来得匆忙,底片还没晾干,就匆匆洗出来。 洗出来以后,送到李家的时候,赵纫兰接过,盯了很久,只说了一句:“好,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