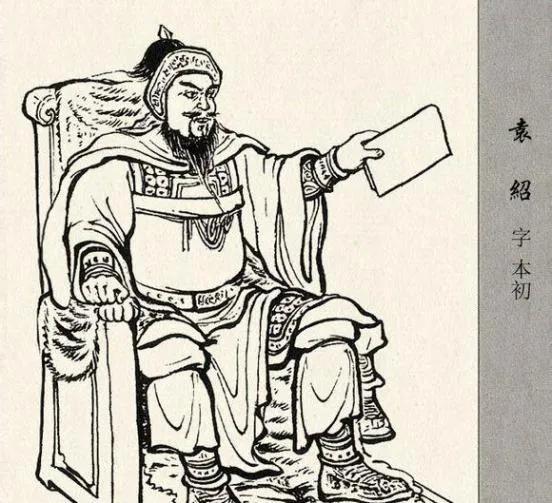1910年,晚清神医自称梦到未来的新中国,没有租界和治外法权,到处高楼大厦,飞船送人上月球,实现了“社会主义”,鲁迅说他胡说八道…… 陆士谔这个人,名气不算大,但在那个时代,敢写敢说的人不少,他算是其中一个。他的本职是医生,但不满足于治病救人,偏要动笔写小说,还写得极有想象力。 他1910年发表的《新中国》小说里,描绘了一个“未来的中国”:彻底废除了不平等条约,没有外国租界,社会公平,科技发达,不仅有飞机,大街上还有“电车”,甚至人类可以搭乘飞船探索太空。 他用“梦”来包装这些设想,说是自己梦到的未来。这种说法看似荒唐,其实是最安全的表达方式。在清朝这个时代,讲这种“未来幻想”是极危险的,他用梦来开脱,实际上是裹挟着大胆的政治主张。 讲真,陆士谔的“预言”之所以被当时的鲁迅批驳,说他“胡说”,不是因为鲁迅看不懂,而是因为当时的现实太惨烈,谁都看不到希望。 那个年代,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洋人横行,百姓受苦,清政府已经是扶不上墙的烂泥。陆士谔敢在这种局势下写出“新中国”的美好图景,自然显得格格不入。 可今天回头看,他所描绘的许多设想,竟然在新中国一一实现了。治外法权?彻底废除。租界?早就收回。高楼?现在一线城市比他想象的还要密集。飞船上天?神舟早就把宇航员送上了太空,嫦娥也奔月了。 而他提到的“社会主义”,这个词汇在清末其实已通过日本等国传入中国。清末很多先进知识分子都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日文译本,对马克思主义也已有初步接受。 陆士谔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阐述社会主义的理论,但他在小说中提到的“人人平等”“没有贫富差距”“政府为人民服务”等理念,本质上与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高度契合。 当时的清政府毫无改革诚意,官僚腐败,陆士谔显然是对这种体制失望至极,才会在小说中幻想出一个全新的国家制度。 鲁迅批评陆士谔,其实也有他自己的立场。鲁迅当时关注的是现实,强调要直面苦难,不愿意用“幻想”来麻醉人民。 他看陆士谔的小说,觉得这是“乌托邦”的幻想,甚至可能让普通人产生“未来会自动变好”的错觉,从而丧失对现实的批判力。 所以他对陆士谔的批评,并不是纯粹否定其内容,而是对其表达方式和效果的担忧。鲁迅是现实主义者,而陆士谔更像是一个希望主义者。 这场“梦境”与“现实”的激烈对撞,恰是清末思想界的生动缩影。彼时,人们既怀揣着对未来的热切渴望,又保有对当下困境的清醒认知,复杂心境可见一斑。 陆士谔的“梦”之所以值得今天我们重读,是因为它不仅反映了时代的压抑,也表达了对未来某种坚定的可能性信念。 我们不能把他的小说简单当作“神预言”,更应该看到他背后的理性思考。他并不是在胡说,而是在用文学的方式提出一个问题:中国有没有可能变得更好? 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确实在很多方面超出了陆士谔的“梦境”。这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偶然,也有时代的必然。新中国的成立,废除了不平等条约,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国家体系,科技发展迅速,社会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有人称陆士谔为“命中注定的预言家”。然而,与其说他精准预言未来,毋宁说他敏锐捕捉到了中国社会“变”的趋势,以超前之姿感知时代发展的暗流涌动。他的“梦”不是迷信,是看到了希望的种子在泥泞中悄悄萌芽。 回头看,陆士谔和鲁迅,一个用幻想表达希望,一个用批判直面现实,他们并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角度不同。两人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剪影。 陆士谔让我们看到,被压抑的年代里,依然有人敢想象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今天能坐在高楼里看着飞船升空,或许也该感谢那个在1910年写下“梦中国”的人。他的“梦”不是空想,而是一种勇气,一种试图跳出时代限制的思维实验。 素材来源:陆士谔《新中国》百年后再版 曾精确预言上海世博(2) 2010年01月25日 14:38 南方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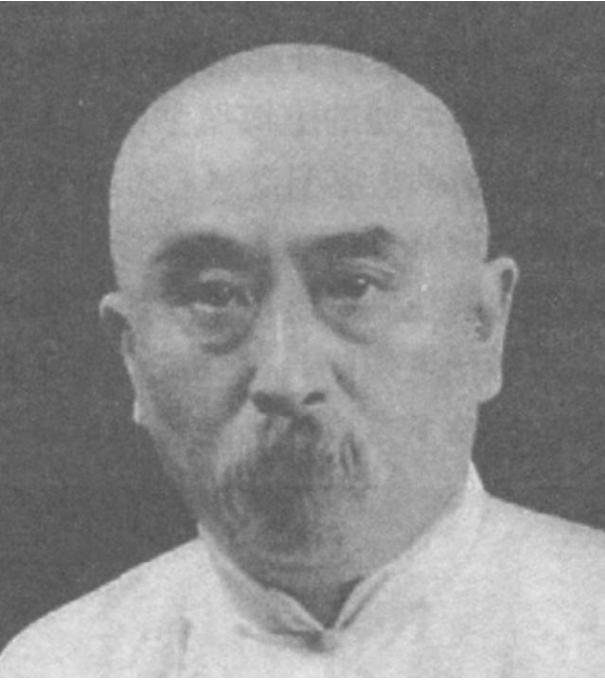


![二十多年前的老照片,认识两人算厉害了吧[滑稽笑]](http://image.uczzd.cn/1077158032667839906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