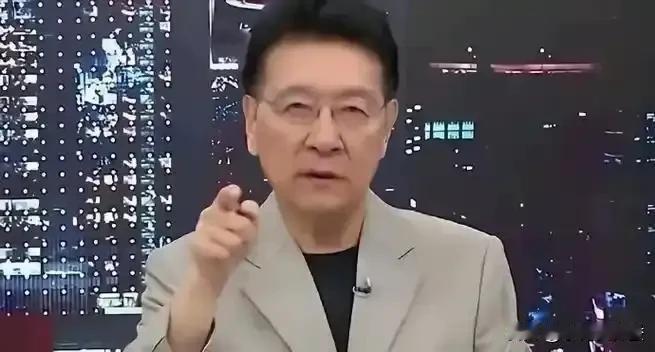2005年,台湾作家徐宗懋找到陈阿菊,对他说:“我受你的妹妹朱晓枫托付,前来看看你。”,85岁的阿菊一听,马上警惕起来,态度极为粗鲁。 2011 年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空调风带着凉意。 朱晓枫捧着朱枫的骨灰盒,盒面 “朱谌之” 三个字泛着微光。 身后传来脚步声,是机场工作人员递来个布包。 “这是台湾陈阿菊女士托人捎来的,说是给您的。”打开布包,里面是条旧羊毛帕,针脚还很整齐。 1949 年冬天,台湾陈阿菊家的煤油灯亮到深夜。 朱枫坐在床边,手里织着小毛衣,毛线是从大陆带来的。 “阿菊,等孩子满月,就能穿这件新衣服了。” 阿菊摸着毛衣领口,笑着点头,没提丈夫的工作。 那时她还不知道,母亲此次探亲,藏着重要任务。 1950 年春天,阿菊发现朱枫的鞋子总很干净。 “妈,您说去菜市场,怎么鞋底没泥巴?” 朱枫愣了下,笑着说 “走的石板路,没沾土”。 夜里,阿菊又撞见朱枫在厨房烧东西,火光映着她的脸。 她心里犯嘀咕,却没敢多问,只觉得母亲不对劲。 几天后,阿菊拉着朱枫坐在院子里。 “妈,您搬走吧,我怕……” 话没说完就红了眼。 朱枫放下手里的针线,摸了摸她的头。 “是妈给你添麻烦了,我这就找地方住。”收拾行李时,朱枫把织了一半的毛衣留在了衣柜里。 1950 年夏天,阿菊和丈夫王昌诚被带走。 “跟朱谌之是什么关系?她有没有跟你说过什么?” 阿菊摇头,说 “就是来探亲的,没说别的”。 关在看守所的几个月,她总想起母亲织毛衣的样子。 出来那天,她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看那件没织完的毛衣。 1951 年,阿菊听说朱枫牺牲的消息。 她瞒着丈夫,偷偷去相关部门打听骨灰下落。 “要领骨灰,得写申请,还得说明关系。”她攥着申请表格,站在门口犹豫了很久。 想到丈夫的身份,最终还是把表格塞进了抽屉。 那份没能说出口的愧疚,成了她心里的结。 1960 年,阿菊整理旧物,翻出个小布包。 里面是朱枫留下的笔记本,记着些家常话。 “阿菊爱吃甜糕,下次带点大陆的糖来。” 看着字迹,她想起小时候朱枫带她买糖的场景。 眼泪掉在笔记本上,晕开了墨迹。 大陆这边,朱晓光一直盼着朱枫回来。 他四处打听消息,却始终没有结果。 随着年岁增长,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却没放弃希望。 2000 年,朱晓光临终前拉着朱晓枫和朱明的手。 “一定要找到你们妈妈,带她回家。” 2001 年,朱晓枫在《老照片》杂志上看到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人很像母亲,她的心一下子揪紧了。 她打听得知,照片是台湾作家徐宗懋找到的。 2003 年台湾养老院,徐宗懋找到她,和陈阿菊见面谈了一会儿。 经过多方努力,2010 年台北辛亥第二殡仪馆,尘埃落在骨灰坛上。 工作人员擦拭坛身,“朱谌之” 三个字模糊不清。 这是朱枫的骨灰,因姓名笔误,在无人区搁置了 60 年。 坛身的裂痕像她一生的坎坷,终于等来了归乡的消息。 消息传到大陆,朱晓枫攥着父亲的旧照片,泪如雨下。 信源:女地下党在台牺牲60年后回家 80岁女儿托人寻母——2011-01-02 08:25:06来源:扬子晚报 《风筝》大结局向她致敬,潜伏后的归家之路她走了60年 2025-06-10 22:57·京报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