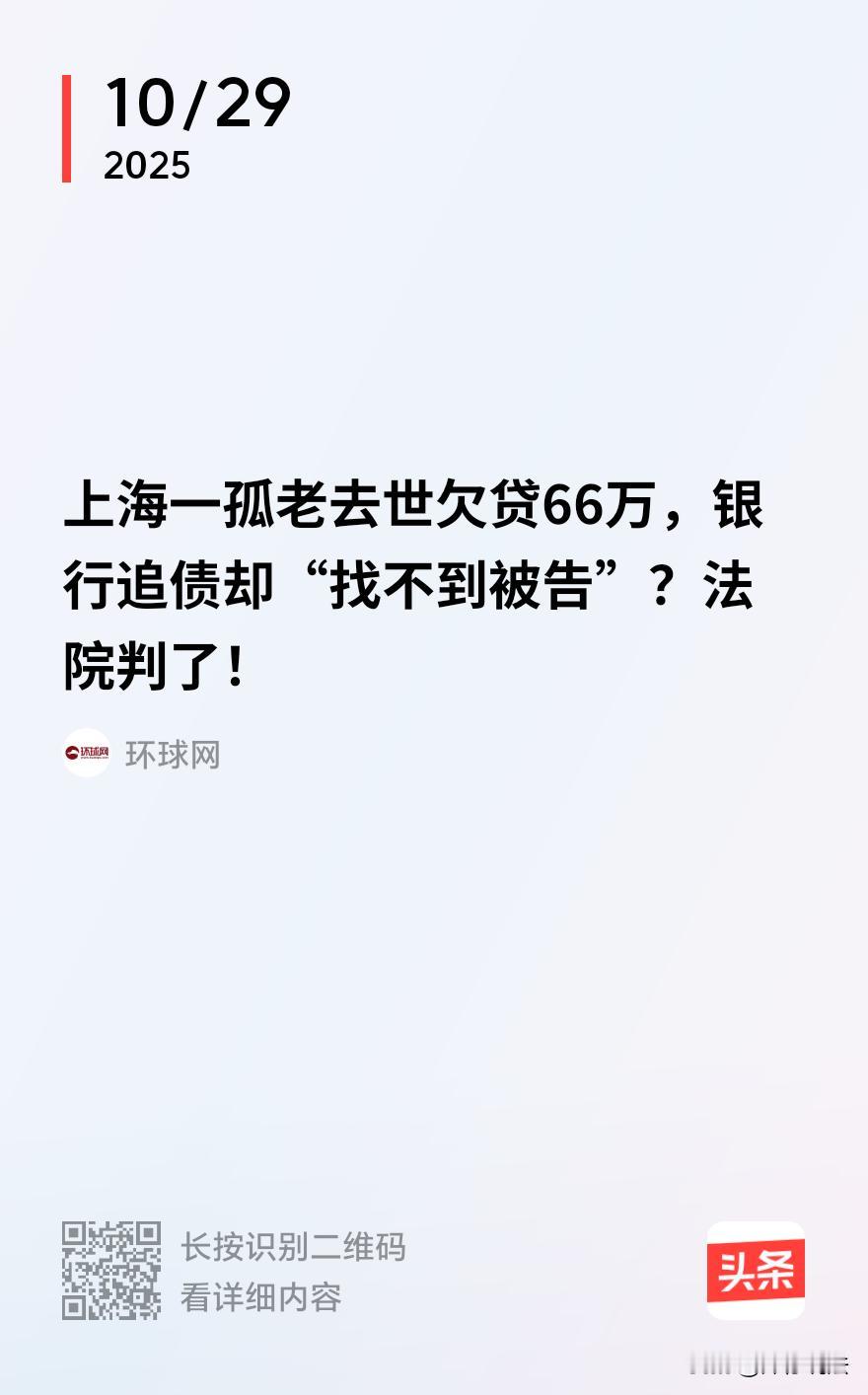上海,一老人膝下无儿无女,生前用房子抵押贷了66万治病。天有不测风云,不到一年,老人突发急病离世,未留下任何遗嘱,没有继承人,这笔债成了“无主之债”,银行想讨债却连被告都找不到。僵局之下,法院指定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家”。银行随后起诉,要求用老人留下的房子清偿债务。法院这样判决。 据悉、宣老老人(化名)年轻时曾是一名普通工人,一生未婚,无儿无女,晚年独自居住在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里。这套房子是宣老唯一的财产,也是他晚年生活的依靠。 2023年初,宣老因身体不适被诊断出患有严重疾病,急需资金治疗和改善生活。于是,他做出了一个决定,以这套房屋为抵押,向当地一家银行申请了一笔最高额抵押贷款,总额度为66万元。 银行审核后,认为房屋价值足够覆盖贷款本金和利息,便与宣老签订了《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 合同约定,宣老可以在授信额度内循环借款,但需按时偿还本息,否则银行有权依法处置抵押房屋。 宣老本以为这笔贷款能帮他渡过难关,但命运弄人。 2024年,宣老因疾病突发不幸去世,未来得及留下任何遗嘱或安排。由于他父母早已过世,兄弟姐妹也无联系,没有任何法定继承人,这笔66万元的贷款很快因无人偿还而逾期。 银行在多次联系无果后,发现宣老已离世,债务陷入了僵局:该找谁追债?按照传统思路,债务人去世后,应由其继承人来承担债务,但宣老偏偏是“孤寡老人”,没有继承人。 银行工作人员一度自嘲:“我们连被告都找不到,这债怎么追?” 银行决定寻求法律途径解决,于是向法院提起了诉讼。但起初,因诉讼需要有明确的被告,可宣老没有继承人,谁来做被告?法院没有立案。 随后,银行先向法院申请指定宣老的遗产管理人。 法院经审理查明,宣老确实无任何法定继承人,且未立遗嘱,于是依法指定民政部门为宣老的遗产管理人。 民政部门被指定为遗产管理人后,银行随即提起了本案的金融借款合同纠纷诉讼,要求民政部门在管理宣老遗产的范围内,清偿剩余的66万元贷款本金及利息、罚息等。 在法庭上,双方展开了辩论。 银行主张,宣老与银行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银行已履行放贷义务,但宣老未按时还款,导致债务逾期。现在,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有责任用宣老的遗产来偿还债务。银行有权对抵押房屋优先受偿。 民政部门则提出了抗辩,他们表示,自己作为遗产管理人,并非债务的直接承担者,而是管理者角色,不应该由其承担任何偿还责任。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一百四十七条规定,遗产管理人应当履行下列职责:……(四)处理被继承人的债权债务;…… 第一千一百六十一条规定,继承人以所得遗产实际价值为限清偿被继承人依法应当缴纳的税款和债务。超过遗产实际价值部分,继承人自愿偿还的不在此限。 法院指出,宣老去世后,没有继承人,理应由宣老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或者村民委员会担任遗产管理人,民政部门已经有法院判决担任遗产管理人,依法应当履行相应职责。 民政部门作为遗产管理人,其法律地位,类似于继承人在继承开始后、遗产分割前的地位,但其职责范围遵循 “限定责任”原则。 这意味着,民政部门对宣老的债务的清偿责任,严格以其所管理的遗产实际价值为上限。 法院认为,民政部门应主动清理遗产、通知债权人,并以遗产清偿依法成立的债务,不能以“非债务人本人”为由拒绝履行。 不过,民政部门的清偿责任严格以宣老遗产的实际价值为限。 如果价款不足以覆盖全部债务,民政部门也仅在此价款范围内承担责任,对于超出的部分,民政部门无需以自身财政资金进行弥补,银行亦不得再向民政部门主张。 此外,《民法典》第三百九十四条关于抵押权的一般规定,以及第四百二十条关于最高额抵押权的规定,物权具有追及效力,不因所有权人的变更而当然消灭。 法院进一步指出,宣老与银行签订的《个人循环授信额度合同(含最高额抵押条款)》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且已依法设立抵押登记,抵押权合法有效。 债务人宣老的死亡,以及其遗产转而由遗产管理人民政部门接管,这一系列变动均属于抵押物所有权的主体变更,但并未损及设立于该物之上的抵押权本身。 银行的抵押权作为物权,其效力追及于抵押物之所在。无论该房产现在由谁名义上管理或未来归谁所有,只要抵押权依法未曾消灭,银行就有权就其行使权利。 最终,法院判决确认,如遗产管理人民政部门未履行判决确定的还款义务,银行有权申请对抵押房产进行折价、拍卖或变卖,并就所得价款在最高债权限额内优先受偿。 同时,法院判决也明确指出,变现后价款超过债权数额的部分,仍属于宣老的遗产,由民政部门继续管理,理论上收归国有。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