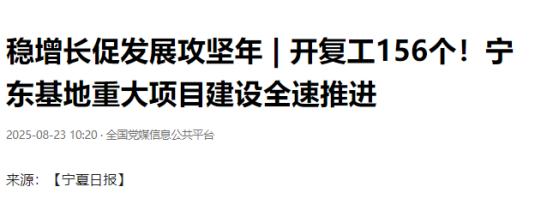1981年两国GDP差不多,印度1930亿美元,中国1950亿美元,到了1982年,印度2000亿,而中国2050亿,又是就差那么一丢丢。 先说说中国这边的“家底是怎么砸出来的”。五十年代跟苏联借援助搞工业那会儿,可不是喊口号热闹。 156个大项目像钉子一样扎在神州大地上,东北的鞍山钢铁厂高炉白天冒浓烟,晚上映红半边天,工人三班倒连轴转,老师傅带着徒弟在轧钢机旁啃干粮;长春一汽的厂房里,第一辆解放卡车下线时,工人们抱着方向盘哭,那是中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 这些项目没白砸,到七十年代末,中国已经能自己造机床、炼钢、产化肥,虽说技术不算顶尖,但重工业的架子立住了,就像盖房子先打了钢筋骨架。 1978年改革开放一启动,这副骨架立马派上了用场。沿海特区刚挂牌,深圳蛇口就炸了锅——招商局的袁庚带着人在荒滩上放炮,喊出“时间就是金钱”,敢跟中组部要政策,帮应聘人才补办档案,连北大教授朱光潜的助手韩邦凯都被吸引来,三个月就解决了夫妻分居难题。 香港商人背着钱袋往深圳跑,台湾老板带着缝纫机到福建办厂,乡镇企业更是像雨后春笋,浙江义乌的农民把鸡毛换成塑料花,广东顺德的作坊里每天产出上万件家电,农民不用背井离乡就能进厂挣工资,连老太太都能在村办玩具厂穿珠子换外汇。 政策松得快,今天说允许个体户开店,明天就给外资办厂开绿灯,产业链说建就建,从零件到组装的配套跟着外资厂子一起长起来,这种“灵活转身”可不是凭空来的,全靠早年重工业攒下的工业基础打底。 再看印度那边,表面GDP追得挺紧,内里早被旧摊子缠成了乱麻。刚独立时继承了英国的官僚体系,好家伙,那套“许可证制度”能把人逼疯。 想开个纺织厂?先去工业部、税务局、土地局等十几个部门盖章,光申请表就得填几十页,企业家带着铺盖卷在政府门口排队,等半年能拿到许可都算运气好。 有个老板回忆,他为了办个饼干厂,跑了七个月,盖了32个章,最后还被要求证明“本地没有同类工厂”,折腾到最后差点把家底赔进去。 尼赫鲁那代搞的公营经济更是雪上加霜,银行、钢铁、电力全被国企垄断,私人企业稍微挣点钱就被“掐脖子”——原材料要从国企买,产品要给国企代工,想扩大规模?没门。 到八十年代初,印度国企占了全国四分之三的资产,产出却只占三分之一,好多工厂里机器锈得转不动,工人上班就是喝茶聊天,亏损全靠政府财政填窟窿,说白了就是借债撑场面。 1981年那1930亿美元GDP里,光外债撑起的泡沫就占了不少,当时印度外债规模已经快摸到GDP的20%,跟中国靠实业攒起来的家底根本不是一回事。 八十年代拉吉夫·甘地上台想改,可步子慢得像蜗牛爬。 说是放松管制,其实也就给进口家电减了点税,电信领域放了个小口子,核心的许可证制度还没动,国企垄断的摊子也不敢碰。 他倒是想扶持IT业,可当时印度连像样的电力供应都没有,电脑开机得先备着发电机,普通工人连键盘都没见过,政策再好也落不了地。 改革只惠及中上层,农民该穷还穷,1987年一场旱灾就让物价飞涨,老百姓怨声载道,加上军火贿赂丑闻缠身,拉吉夫没干几年就下台了,所谓的改革也就不了了之。 说到底,1981年那“一丢丢”的差距,从来不是数字游戏。中国是先砸重工业打底子,再靠改革开放松绑激活,像辆保养好的卡车,踩油门就能往前冲;印度则是背着官僚体系的包袱,拖着公营经济的沉疴,就算想加速,也被旧框架捆住了手脚。 后来的差距越拉越大,根本不是运气问题——一个敢破敢立,把政策灵活性和工业底子结合得死死的;一个墨守成规,旧毛病没治好又添新麻烦,这“差一丢丢”的背后,早就是两条道上跑的车了。 现在再回头看那段数据,与其说中印曾经站在同一起跑线,不如说中国早早就选对了跑道。 工业奠基是“扎深根”,改革开放是“长枝叶”,两者凑在一起才有了后来的经济腾飞;而印度直到今天,还在为当年没理清的官僚体系和公营经济问题头疼,这也印证了那句老话:路选对了,慢点开也能到;路选错了,再使劲也白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