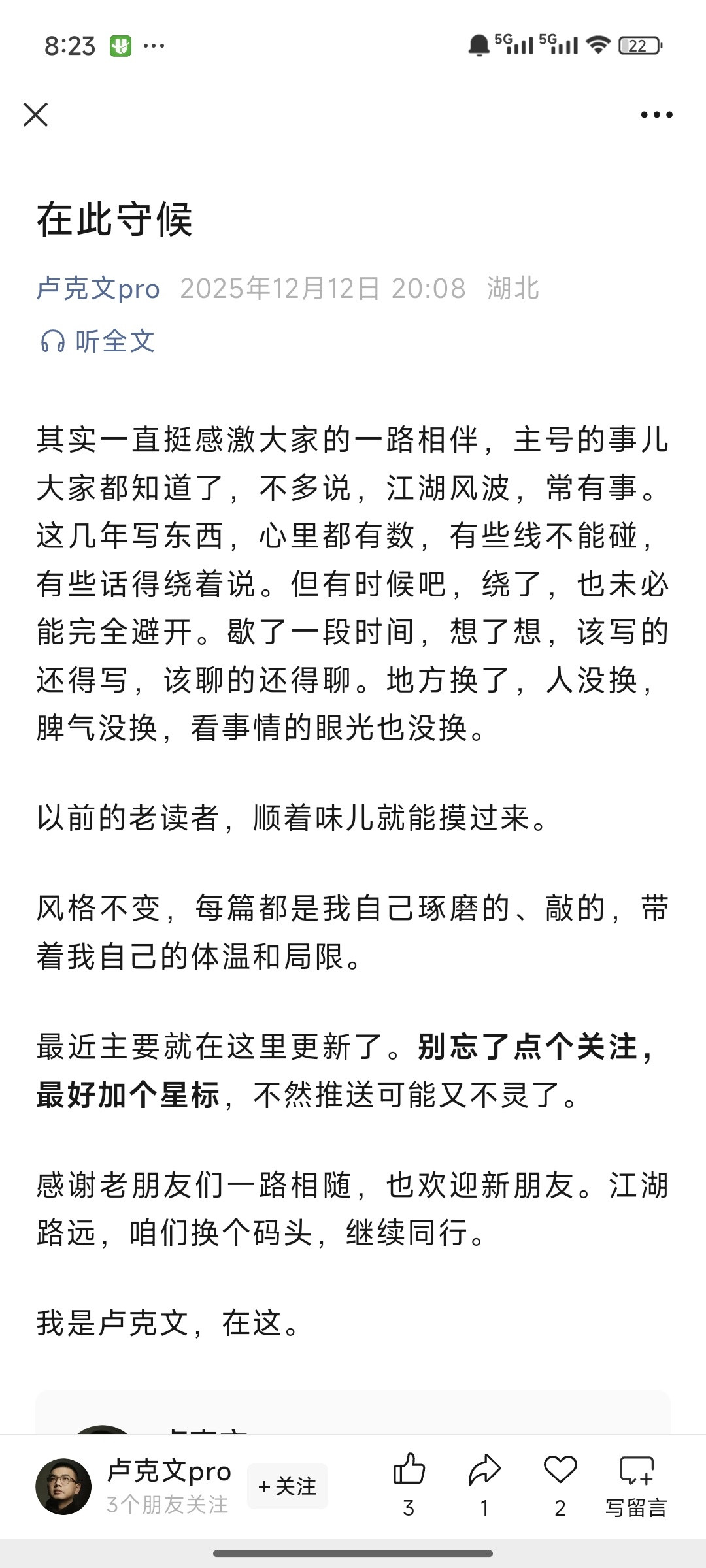1956年,科学家将一只公鼠与5只母鼠放在一起,发现公鼠会与所有母鼠繁衍后代,然后进入“贤者模式”,除非再放入一只新的母鼠,否则它几乎不会在短时间内继续交配。 这只公鼠突然停下了动作。 原本在繁殖箱里活跃了整整三天的它,对身边的五只母鼠失去了所有兴趣,连最活跃的那只靠近时,它也只是转过脑袋躲开。 直到研究人员放入第六只陌生母鼠,这只看似倦怠的公鼠突然像被按下重启键,瞬间恢复了最初的亢奋状态。 科学家给这个现象起了个名字,库里奇效应。 这个源自美国总统轶事的术语,道破了生物界一个藏了万年的秘密:我们对新鲜感的渴求,可能写在基因最深处。 2008年有研究发现,野生大猩猩种群里,雄性首领每过三五年就要换配偶,比例高达八成以上。 就连采蜜的工蜂,对同一朵花的访问频率都会随着时间下降四成,好像大自然早就给每个物种装了“喜新厌旧”的程序。 人类似乎也没跳出这个逻辑。 哈佛大学在1972年做过个有趣的实验,请两百人连续选五轮约会对象,近九成受试者每轮都选了不同的人。 后来脑成像技术发现,看新面孔时大脑伏隔核的多巴胺分泌量,比看熟人时高出两倍多。 现在的电商平台就很懂这个道理,同一牌子的香水,能让消费者回购第二次的还不到三分之一。 但我们和老鼠终究不一样。 2018年《神经科学杂志》发过篇论文,说人类前额叶皮层对冲动的控制力,比黑猩猩强三倍多。 这种生理结构差异,让我们能主动对抗本能。 就像17世纪的伦勃朗,对着镜子画了三十年自画像,从青年画到老年,把同一张脸画出了岁月的厚度。 我觉得这种在重复中挖掘深度的能力,正是文明和本能最大的分野。 斯坦福大学跟踪研究了四十年的实验很能说明问题。 那些能忍住不吃棉花糖的孩子,长大后成功率比别人高不少。 日本的终身雇佣制、德国的双元制教育,都是在制度层面培养这种“反本能”的能力。 今年欧盟新出的《数字伦理法案》更有意思,要求社交媒体必须设置“专注模式”,就是怕我们在无限滑动里迷失了方向。 当那只公鼠再次对新母鼠兴奋时,我们却能用理性按下暂停键。 这种把短暂冲动转化为长期价值的能力,藏在伦勃朗层层叠叠的油彩里,藏在那些愿意深耕一个领域的职场人身上,也藏在每个主动关掉推送提醒的深夜。 或许这就是人类最特别的地方,我们既能听懂基因的低语,更能写出自己的旋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