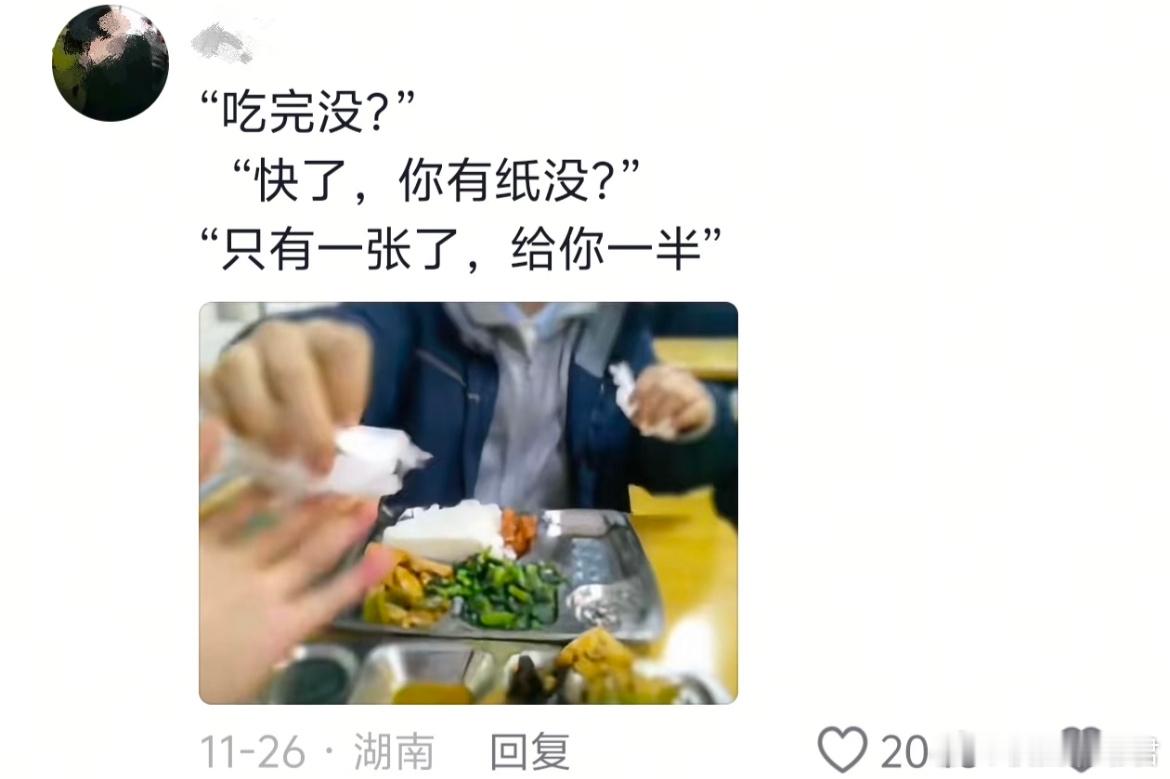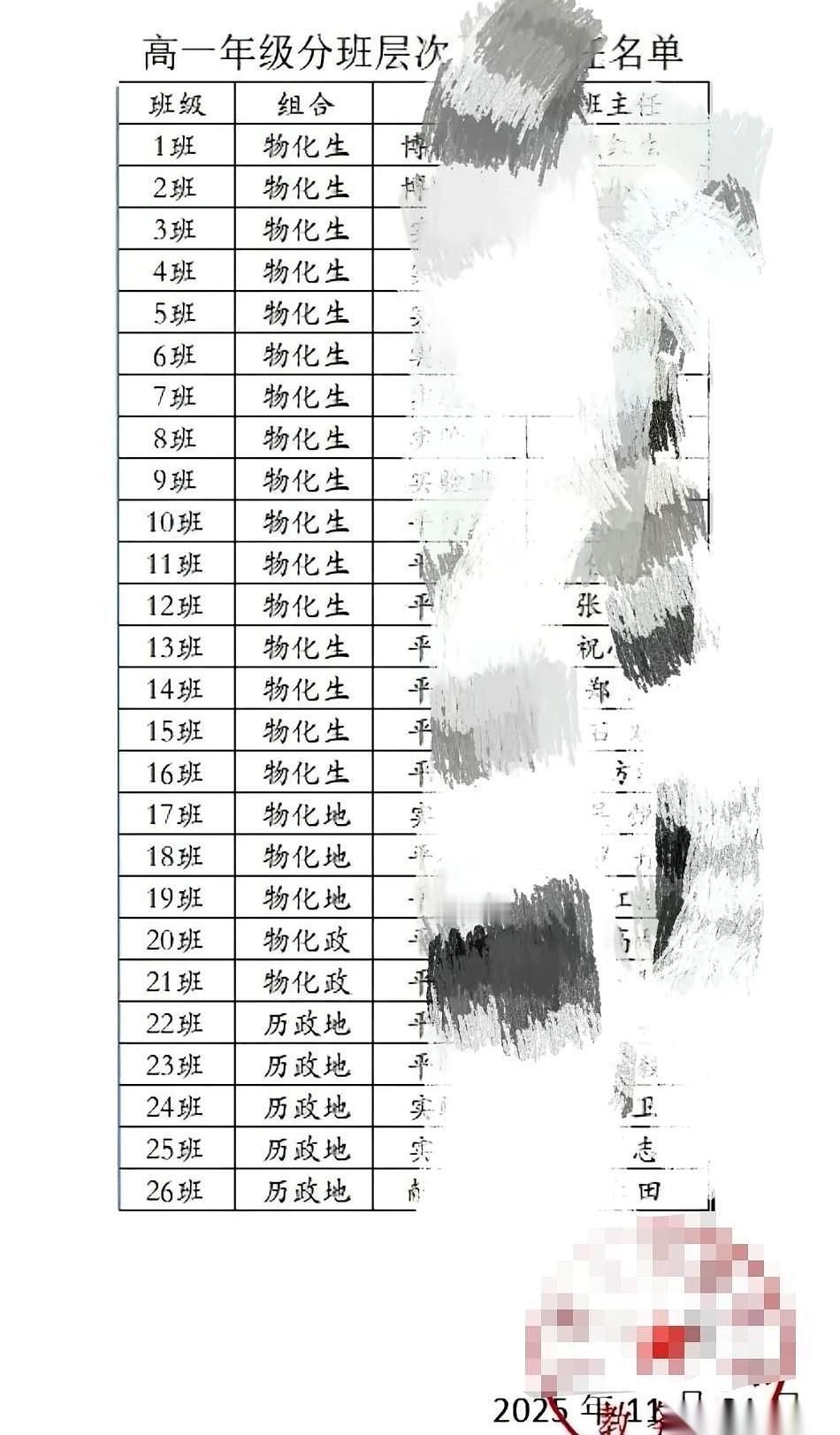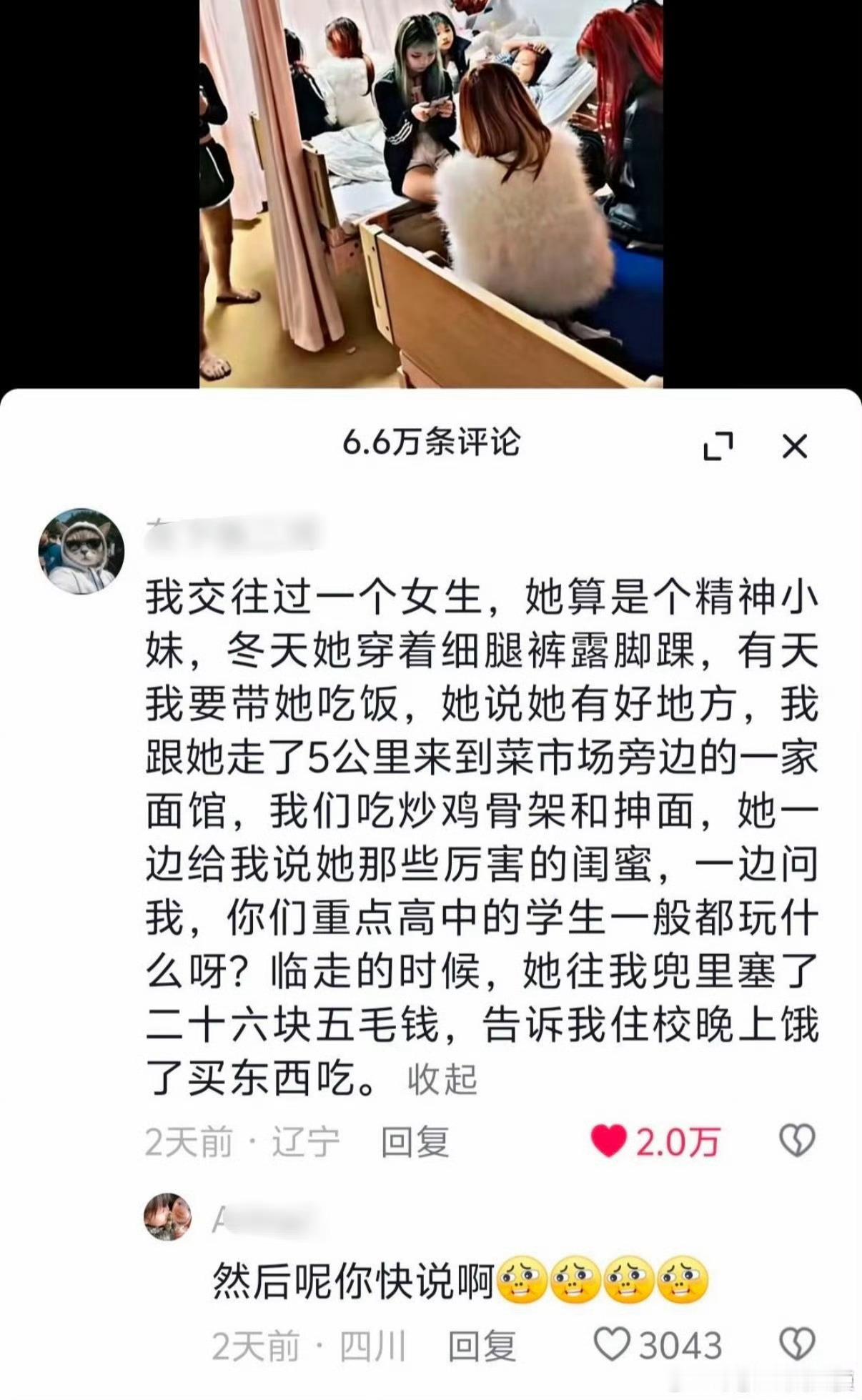又是一年中考时今天是中招考试的最后一天了,闲来无事,忽然又想起了那年中招带考的情景。多年前,中招带考。学生进考场后,我们几个送考老师来到学校大门外的树荫下乘凉。 又是一年中考时。 窗外的蝉鸣突然密起来,跟多年前那个下午一模一样。 那年我还是个刚带完第一届毕业班的班主任,跟着其他几个老师站在考场外,看学生们抱着文具袋往教学楼里走。最后一个男生回头冲我挥了挥手,校服领子歪在一边,像只急着起飞的小麻雀。 校门“哐当”一声关上时,我们几个像被抽走了主心骨,稀里糊涂就挪到了大门外那排老槐树下。 树荫浓得化不开,阳光从叶缝里漏下来,在地上拼出晃动的光斑。王老师从包里摸出袋瓜子,嗑了没两下又塞回去,“别吵着里面”;李老师拿手帕擦额头的汗,其实那天风挺凉,凉得能吹起她鬓角的白头发——她带毕业班带了二十年,比我们都懂这种“等”的滋味。 手里攥着的保温水杯早没了凉意,冰块融成的水顺着杯壁往下滑,滴在水泥地上洇出小小的深色圆点,像我们悬着的心,一下一下往下沉。谁也没多说话,可眼睛都往教学楼的方向瞟,连飞过的麻雀落在栏杆上,都要盯着看半天。 “其实不用这么紧张,”体育组的张老师突然开口,声音有点哑,“孩子们平时练得够扎实了。” 没人接话。他自己先笑了,从裤兜里摸出个皱巴巴的烟盒,又想起这是学校门口,悻悻地塞回去,“我儿子当年中考,我在这儿站了仨小时,腿都麻了。” 后来才知道,那天我们几个站的位置,树荫刚好能把整栋教学楼的入口框进去,像个天然的取景框。框里的人在奋笔疾书,框外的人在数着秒等。 大概是下午三点半,教学楼的门突然开了条缝。 第一个冲出来的是我们班的小个子女生,扎着高马尾,校服裙摆被风掀起来。她没直接跑向校门口,反而绕到我们站的树荫下,仰着脖子喊:“老师!作文我写的‘那一刻,我长大了’!” 声音脆生生的,带着点没藏住的得意。我们几个突然就笑了,刚才还紧绷的肩膀一下子松下来,王老师伸手想揉她的头发,又想起她刚考完试,手在半空停了停,改成拍了拍她的胳膊。 陆陆续续有学生出来,有的红着眼圈说“数学最后一题没写完”,有的举着准考证欢呼“我检查了三遍”,还有的凑到我们身边,叽叽喳喳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拍毕业照”。 夕阳把树影拉得老长,我们几个被学生们围在中间,听着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考试、说暑假、说以后想考的高中,手里的水杯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接过去,又被谁灌满了温水递回来。 你说我们当年在树荫下等的,到底是他们的考试结束,还是我们自己那段拧着劲儿的时光落下帷幕? 后来带过很多届毕业班,送考的场景换过不同的学校、不同的树,甚至连蝉鸣的调子都好像变了些。可每次站在考场外,总觉得脚下的水泥地还是当年的温度,手里的水杯还是当年那个没了凉意的触感——后来才明白,那不是煎熬,是我们和少年们共享的最后一段“并肩而不言语”的默契。 短期看,那天下午的等待不过是让我们多站了三个小时;往长了说,是那些蝉鸣、树荫、没说完的担心,和少年们跑出来时带着汗的笑脸,一起酿成了后来每次想起都觉得暖的酒。 现在路过中学校门口,看到家长们挤在树荫下,手里攥着水和纸巾,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教学楼,就会想起当年的我们。其实不用劝他们“别紧张”,有些等待啊,本就是陪着别人长大时,自己悄悄学会的温柔。 风又吹过来,窗外的蝉鸣停了片刻。 我好像看见多年前那个下午的树荫里,几个年轻的老师和一群更年轻的少年,正隔着时光,对现在的我,轻轻笑呢。
后来,我们再也找不到高中时候的感觉了
【12点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