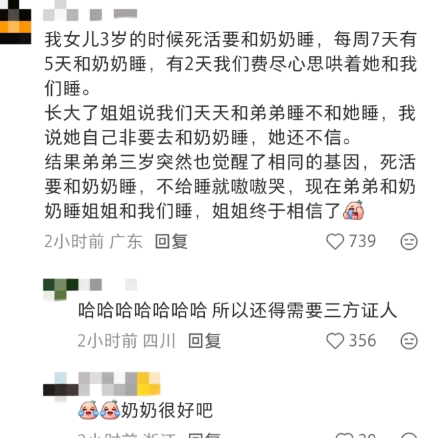70多岁的老人拄着拐杖,在老胡同里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过往的碎片上。 他要去的地方,是当年被他伤害过的人家门口,手里攥着的纸条写了又改,最后只剩“对不起”三个字。 深秋的风卷着落叶打在他脸上,他却没抬手挡,好像这样能让心里的沉重轻一点。 医生说他的腿疾不适合多走动,可他不听。 从城东边的老房子到城西的胡同,单程就要一个多小时,他每周都去。 有次在楼下等了两小时,对方始终没开门,他就把写着道歉的纸条从门缝塞进去,转身时背影驼得更厉害了。 这样的事发生过不止一次,他却从没说过“放弃”两个字。 从权力巅峰退下来后,他住进了普通的老房子,墙上没挂一张过去的照片。 有人说他是在逃避,他却在日记里写:“现在才看清,当年站在台上时,眼睛里全是影子,脚下全是深渊。” 这种角色的落差像一把钝刀,慢慢割开了被时代裹挟的麻木,让那些被忽略的细节一点点浮现,某个人的眼泪,某个家庭的破碎,都成了夜里睡不着时的常客。 后来他开始写东西,台灯从晚上亮到凌晨,稿纸堆在桌上像座小山。 本来想把所有错误都写进书里,后来发现最该说的,还是当面那句“对不起”。 书名叫《十年一梦》,里面没有华丽的词藻,只有会议记录的片段、当时的日记摘抄,还有现在的批注。 他在某页写:“那时以为自己在做正确的事,后来才明白,‘正确’两个字,需要用良心打底。” 书出版后,他没送过熟人,只寄给了几位当年的受害者。 有位老人收到后,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字里行间的颤抖,我读得懂。” 这句话让他在沙发上坐了一下午,窗外的麻雀停在晾衣绳上,他忽然想起年轻时,也曾这样安静地看过天,只是那时心里装的是别的。 74岁那年冬天,他突发疾病住院。 病床前,他拉着儿子的手说:“把我的遗体捐了吧,算是最后做点有用的事。” 儿子愣了愣,想起父亲这些年的奔波,想起书里那些被红笔圈住的“愧疚”,最终点了头。 2007年10月,他的名字出现在医院的遗体捐献名录上,备注栏里写着“无特殊要求”。 《十年一梦》的手稿后来被档案馆收藏,最后一页有行铅笔字:“若有来生,愿做个普通人,守着一盏灯过一生。” 而他捐献的遗体,在医学院的实验室里,成了沉默的教材。 那些曾经被他伤害的人,或许永远不会完全原谅,但当学生们对着标本轻声说“谢谢”时,某种迟到的和解,正在时光里慢慢生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