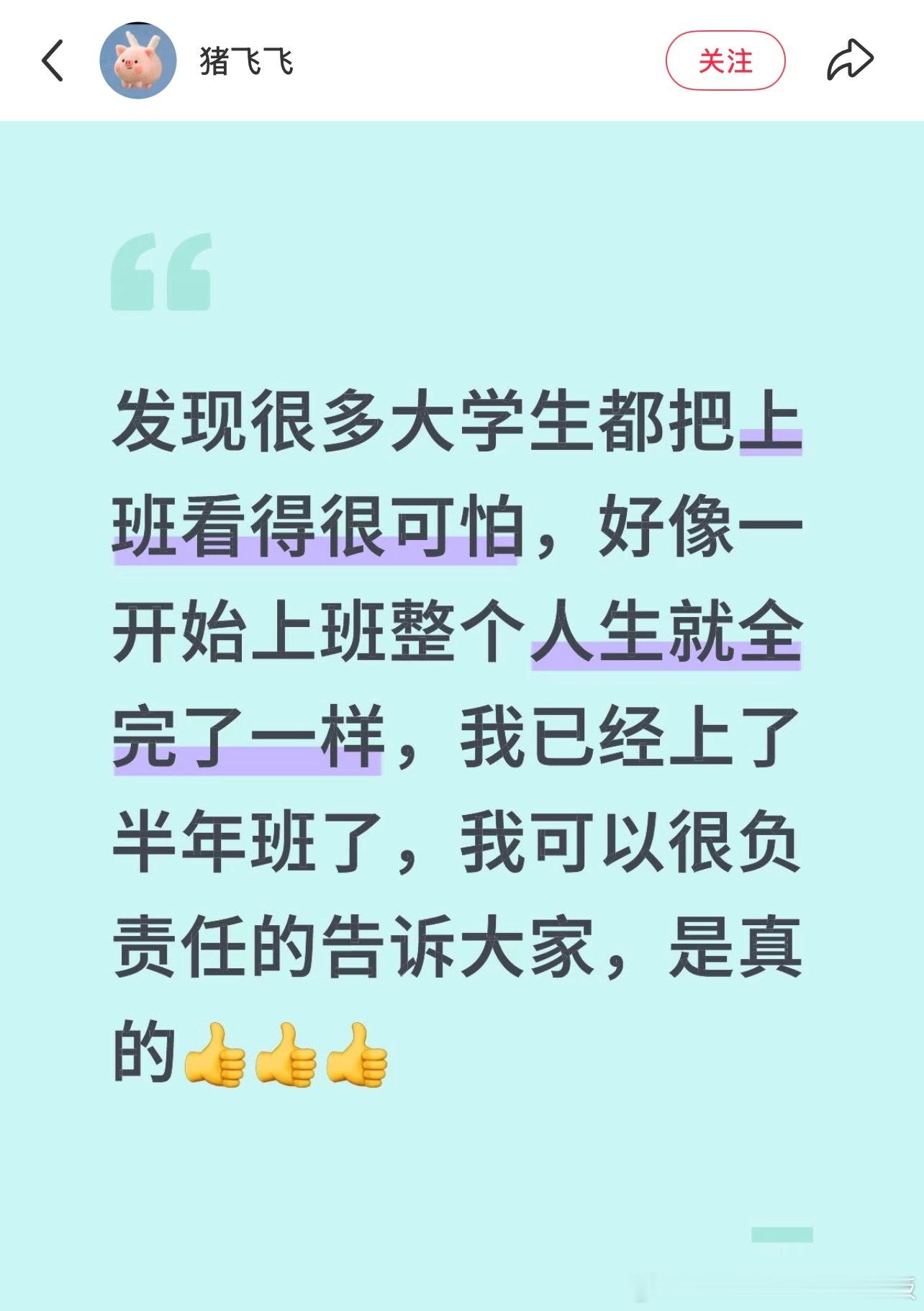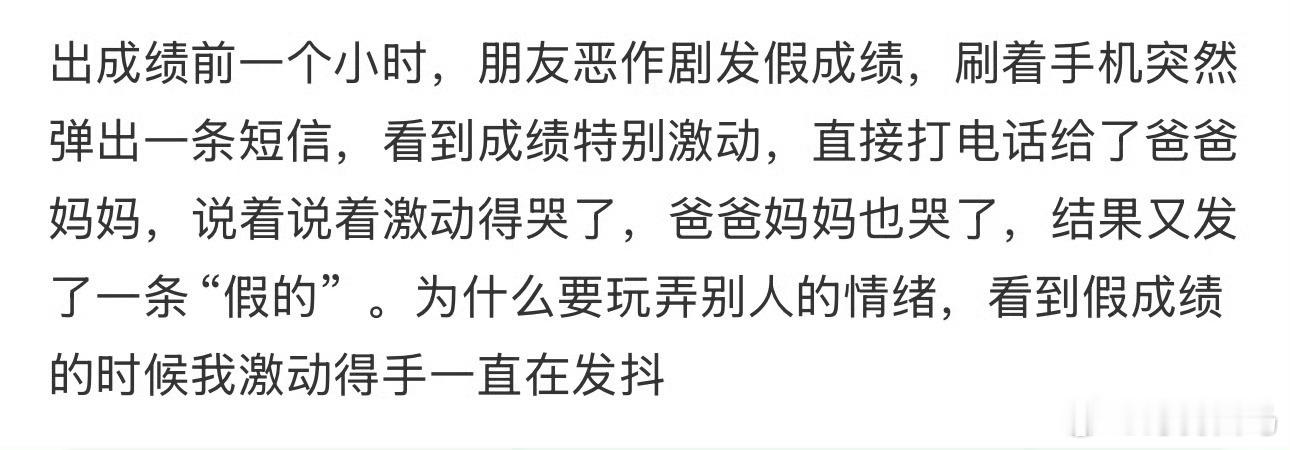1965年的江苏乡下,一张印着"不宜录取"的初中报名表在少年手中微微发颤。 他攥着全乡第一的成绩单站在公社办公室外,听见里面说"成分不好的孩子,书念得再好有什么用"。 那张被退回的报名表边角已经磨出毛边,钢笔写的"优秀"评语和红色印章挤在一起,像个刺眼的笑话。 少年把纸折成方块塞进裤兜,走在回家的土路上,蝉鸣吵得人心烦。 书包里还装着昨晚没做完的数学题,现在看来,未知数x大概和他的未来一样,永远也算不出解。 那时候的学校门口总贴着"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标语。 老师私下塞给他一本旧字典,说"知识总有用",但转头又在班会上强调"红五类子女要带头努力"。 他看着同桌王建军,村支书的儿子,数学考38分却拿着重点高中的保送表,铅笔盒里还刻着"革命接班人"五个字。 后来才知道,不光是升学。 表哥在县城工厂当学徒,转正时因为"祖父是地主"被刷下来;邻居家daughter想参军,政审表上连外祖父的成分都查了三代。 整个村子像个密不透风的玻璃罐,标签贴在额头上,想透气都难。 他学着往稻田里撒化肥时,收音机里正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本来想跟着去东北碰碰运气,但后来发现农垦团招工也要查八代成分。 赤脚医生说他手指长适合拿手术刀,这话让他在田埂上坐了半夜,露水打湿了补丁摞补丁的裤脚。 1977年冬天,他在广播里听到恢复高考的消息,正在给麦苗浇水的瓢"哐当"掉在井边。 跑到公社供销社买报名表时,钢笔没水了,借的会计的红墨水,写名字时手直抖。 这次表格上没有"家庭成分"那一栏,只有"报考志愿"和"考试成绩"。 现在孙子翻出他当年的准考证,塑料皮都脆了。 照片上的青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别着枚"为人民服务"的像章,那是王建军后来送他的,说"以前对不起"。 我觉得,当一张没有成分栏的准考证能代替所有标签时,那些在田埂上坐过的夜晚,才算真正结出了果实。 上个月整理老屋,在樟木箱底发现那张1965年的报名表。 红笔写的"不宜录取"四个字洇开了,和后来用红墨水填的高考报名表放在一起,像两页翻不过去的日历。 阳光从窗棂照进来,在"考试成绩"那一栏上,新的钢笔字把旧的评语盖得严严实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