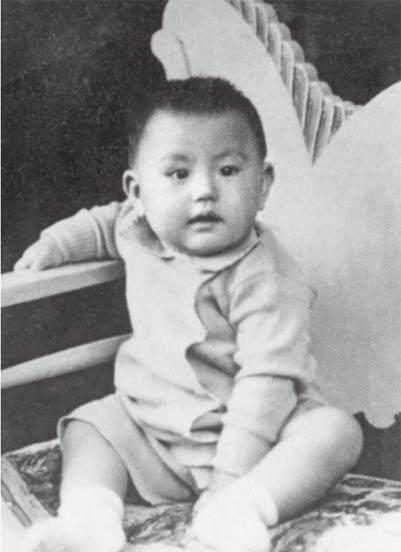1945年延安,社会部夏之栩一拍桌子,冲一个八九岁的小女孩大声问道:“你到延安来做什么?” 小女孩叫吴铁梅,刚结束二十多天的昼伏夜出,从冀东根据地辗转到延安。她的小布鞋沾满泥点,裤脚还别着半片没来得及摘下的酸枣叶——那是穿越封锁线时挂在荆棘上的。 母亲本是冀东游击队的交通员,1944年深秋那场杨家铺突围后,带着她在山沟里打游击;1945年初母亲接了新任务,才把她托付给过路部队,让她去寻在中央情报部工作的父亲吴德。 这不是铁梅第一次直面生死。两岁多坐在家门口玩拨浪鼓时,就被父亲的叛徒同事抱到海边,倒提着浸进咸涩的海水里逼问住址。母亲疯了似的冲过来夺人时,她的蓝布兜肚还在滴水,手里却死死攥着那只掉了漆的拨浪鼓。 1943年更难熬。母亲被日军抓走后,她和姥姥躲在村外草棚,两天没吃东西晕过去。姥姥摸着黑钻进地主的花生地,刨出一把带泥的嫩果,用衣襟擦吧擦吧塞给她——那点涩味,是她对“活着”最原始的记忆。 去年在丰润县夏庄子村,日军的“铁壁合围”来得突然。母亲抱着她骑上毛驴往村外冲,枪声像炒豆子般在耳边炸开。过壕沟时她一头栽进沟里,醒来时满天星斗,沟底的枯草垫着她,警卫员正用衣角擦她脸上的泥——母亲后来总说,那是老天爷把她从枪林弹雨中“捡”回来的。 夏之栩的南方口音让铁梅发懵。“你个人有什么志愿?”“愿意学习还是工作?”连串问题像打闷雷,她只看见对方胸前的搪瓷缸子在晃。直到那句拍桌子的质问炸响,她才红着眼圈憋出一句:“我来找爸爸。” “你爸爸叫什么?” “吴德。” 夏之栩手里的钢笔“啪嗒”掉在登记表上,墨点晕开像朵乌云。她忽然凑近捏住铁梅的下巴左右端详,随即笑出声:“这倔眉眼,跟你爹一个模子刻的!”电话接通时,铁梅听见对方说“让她等着,我马上到”,那声音和母亲夜里偷偷拿出来的、磨得发亮的旧照片背后的字迹一样,带着河北丰润的乡音。 战乱年代,有多少这样的骨肉分离最终成了永别?铁梅的妹妹生下来不足百天,就被寄养在滦县南关村的工人家里,父母抗战胜利后回去找时,那户人家早已搬走,只留下个空荡荡的土炕。 那天下午吴德冲进社会部时,铁梅正趴在桌边看夏之栩办公,手里无意识地摩挲着桌角的木纹。后来她在延安保小读书,课本里夹着父亲写的字条:“别怕走夜路,星星会给咱照道。” decades后,吴铁梅在文物研究所整理父亲遗物,翻出那本1945年的登记表,夏之栩批注的“眉眼如父,性似顽石”旁边,不知何时被父亲画了个小小的拨浪鼓——和她两岁时攥在手里的那只,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