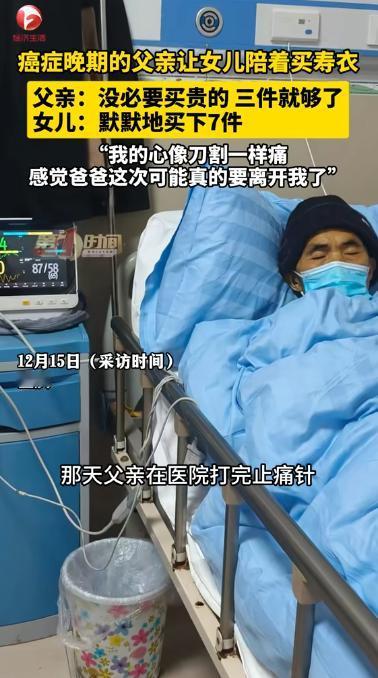大约 80 年代末,一个中医院的医生用一个大澡盆,把绦虫病人坐进去,不断加热水,保持体温的温度,慢慢引着绦虫爬出病人肛门,最后一米多长,我听的时候,都快呕吐了。 这事是爷爷蹲在供销社门口的石墩上,吧嗒着旱烟跟我说的。那年我刚上小学,暑假去爷爷那儿住,他总爱讲些镇上的稀罕事,唯独这件,说得他直皱眉,说“瘆人,但也救人”。 爷爷说的病人叫老李,邻村的庄稼汉,四十多岁,以前常来供销社打酱油、买化肥。我爷对他印象深,是因为开春时他来买尿素,穿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后襟被风掀起,能看见脊梁骨像串算盘珠子似的凸着,褂子空得能塞进另一个人。 “那时候还能笑呢,”爷爷磕了磕烟灰,“说‘今年雨水好,该能多打两袋粮’,露出的牙床都硌得慌。”可到了芒种,老李再来买镰刀,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颧骨尖得能在墙上刻痕,付账时手都抖,钱票掉在地上,弯腰捡都费劲,我爷扶他一把,摸到胳膊上的肉薄得像层纸。 村里人都说老李是“被啥东西吸了精气”。白天在地里割麦,疼得抱着肚子在垄沟里打滚,冷汗把土都洇湿了;夜里更惨,媳妇说他蜷在床上哼哼,像头受伤的牲口。去县医院,化验大便说是绦虫,开了打虫药,吃了蹲厕所蹲到腿软,拉出来点白丝丝,以为好了,没几天疼得更凶,拉得更勤,眼瞅着就剩层皮裹着骨头。 “西药咋就不管用?”我当时插嘴问爷爷。爷爷捻灭烟头,说有人背地里议论,是不是虫子太大,药劲不够,“也有人说,那虫子在肚子里待久了,跟人‘熟’了,药杀不死”。直到有天,老李媳妇借了辆二八大杠,驮着老李往镇上赶,二十多里土路,车胎都瘪了半截,到老街口“王记诊所”时,俩人裤腿全是泥。 王大夫的诊所就一间小平房,药柜抽屉上的红纸药名磨得发亮。他给老李把完脉,慢悠悠说:“虫太大,吃药打不下来,得引。”引?老李当时就懵了。第二天一早,王大夫烧了一大锅热水,找了个黑黝黝的木澡盆——就是农村洗澡用的那种,边缘磨得发亮。让老李脱了裤子坐进去,水温调得跟体温差不多,旁边放个暖水瓶,凉了就添热水。 “就坐那儿?”我追问。爷爷点头,说王大夫搬个小板凳坐旁边抽烟,老李媳妇站门口攥着手。坐了快一个钟头,老李突然“哎哟”一声,说屁股眼那儿痒痒的,有东西往外钻。王大夫赶紧按住他:“别动!一动就断,头留里头还得长!” 那虫子慢悠悠爬出来,白花花的,身上有纹路,王大夫拿竹片轻轻拨着,一圈圈盘在盆边,像条小蛇。后来一量,一米二长,老李瞅见当场就吐了,他媳妇直接跑出去蹲在墙根干呕。王大夫拿棉线系紧虫尾,让老李带回家埋了,又开了几副汤药,“养养身子,别喝生水”。 俩月后,老李又来供销社了。爷爷说他差点没认出来:脸上有了血色,腮帮子鼓了点,穿那件旧蓝布褂子不晃荡了,买了二斤红糖、一包槽子糕,说是给王大夫送礼。“现在一顿能吃俩馒头,”老李笑着拍我爷肩膀,力气大得差点把我爷拍坐地上,“前儿个割豆子,割了半亩地都不喘气!” 有人说这法子土,不科学,可老李实实在在好了。那时候农村医疗条件差,县医院治不了的病,老中医一个澡盆、一锅热水就解决了。现在想想,老李从瘦得像根柴到能扛麻袋,靠的不只是热水和澡盆,或许还有那代人面对病痛时,一点都不敢浪费的希望吧。 那天爷爷讲完,我扒拉着碗里的面条,突然觉得嘴里没味。不是因为虫子恶心,是想起老李媳妇驮他看病时,瘪了半截的车胎——那代庄稼人的日子,咋就这么重呢?
大约80年代末,一个中医院的医生用一个大澡盆,把绦虫病人坐进去,不断加热水,
小依自强不息
2025-12-17 18:21:45
0
阅读: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