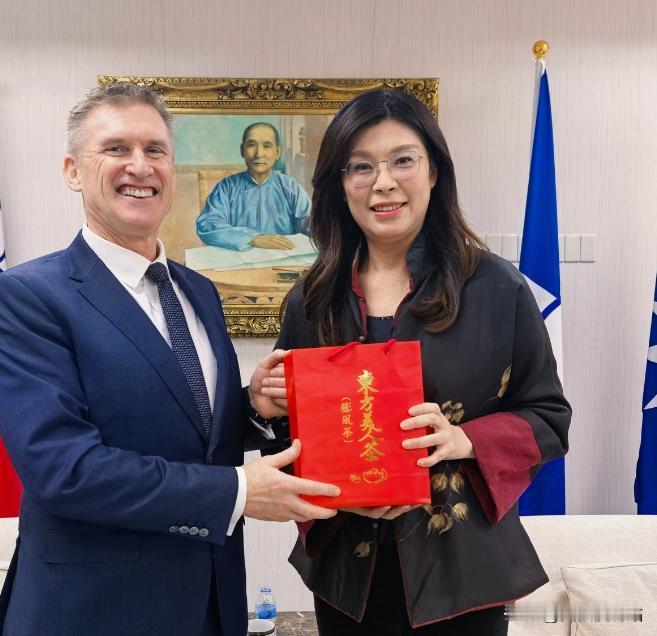1978年7月,胡乔木提出一个在当时看来石破天惊的观点,即:“社会主义制度不能自动地保证国民经济有计划和高速度地发展。”他的这番言论,很让一些思想僵化的人们反感,并且大肆攻击。 会议室里的搪瓷缸子被重重顿在桌上,茶渍溅到“阶级斗争为纲”的学习材料上——这是国务院务虚会现场,有人指着胡乔木的发言稿质问:“这不是在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吗?” 这样的质疑并非偶然。1912年生于江苏盐城的胡乔木,早年间从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到浙江大学外国文学系,没毕业就带着一箱子进步书籍投身革命。1937年到延安后,他在毛泽东身边整理文件,常常在窑洞油灯下逐字核对政策文稿,连标点误差都用红笔标出——这种对理论细节的较真,后来成了他打破思维桎梏的利器。 1977年恢复工作时,55岁的胡乔木接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书架上很快堆满《资本论》批注本和各地经济简报。他在一份1976年农村调查报告空白处划了道粗线:“人均年收入125元,口粮不足200公斤”,旁边写着:“制度再好,违背规律也会饿肚子。” 难道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真的不需要尊重经济规律就能实现吗?面对质疑,胡乔木没有回避。他在务虚会上摊开1958年的炼钢数据:河南农村土高炉炼出的铁锭,三分之二脆如瓦片,农民家里的铁锅却被砸得只剩饭勺;1961年全国粮食产量比1957年跌了四分之一,供销社货架上的肥皂要凭票供应——这些数字像针一样刺破“制度自动论”的泡沫。 他进而提出更“离经叛道”的建议:要学市场经济里的“有用经验”,比如专业公司怎么组织生产,现代银行怎么调控资金,甚至计量经济学怎么算投入产出。这些话让会场瞬间安静,有人悄悄把笔记本翻到“警惕资本主义复辟”那一页。 胡乔木却从公文包里抽出《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讲‘商品经济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我们连价值规律都不承认,怎么谈优越性?”这句话让争论转向,也让邓小平在会后拍板:“乔木的意见,要组织人好好研究。” 得到支持的胡乔木没歇着。他带着社科院的团队南下,在上海江南造船厂蹲了三天,车间主任递来的生产日志上,“完成国家指标”五个字被圈了又圈,后面却用铅笔写着“实际损耗超计划30%”。在天津外贸公司,老会计翻开账本叹气:“出口袜子按统一定价,好棉坏棉一个价,谁还愿意做精品?”这些细节都被他记进调研笔记,最后凝结成《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初稿。 七易其稿后,1978年10月6日,这篇文章登上《人民日报》头版。印刷厂的排字工发现,“市场经济”四个字第一次没有被打上引号;安徽小岗村的农民把报纸上“利润留成”四个字剪下来,贴在生产队的墙上;日本《朝日新闻》驻华记者在发回的电报里写:“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信号,藏在这篇5000字的长文里。” 三个月后,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转到经济建设。又过六年,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突破4亿吨,工业总产值比1978年翻了一倍还多。当年攻击胡乔木的声音,渐渐被工厂里的机器声、田野里的收割机声盖了过去。 1992年9月,胡乔木在北京逝世。他的书桌上,那本《资本论》还夹着1978年的调研车票;书架最上层,摆着1984年的粮食产量报表。2018年改革开放四十周年时,党史研究者这样评价:他用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敲开了尊重规律的门缝——而后来的每一步发展,都从这道门缝里,照进了现实的光。

![网友预测的五年后的全球政治格局,你赞同吗?[思考]](http://image.uczzd.cn/13583973757169343106.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