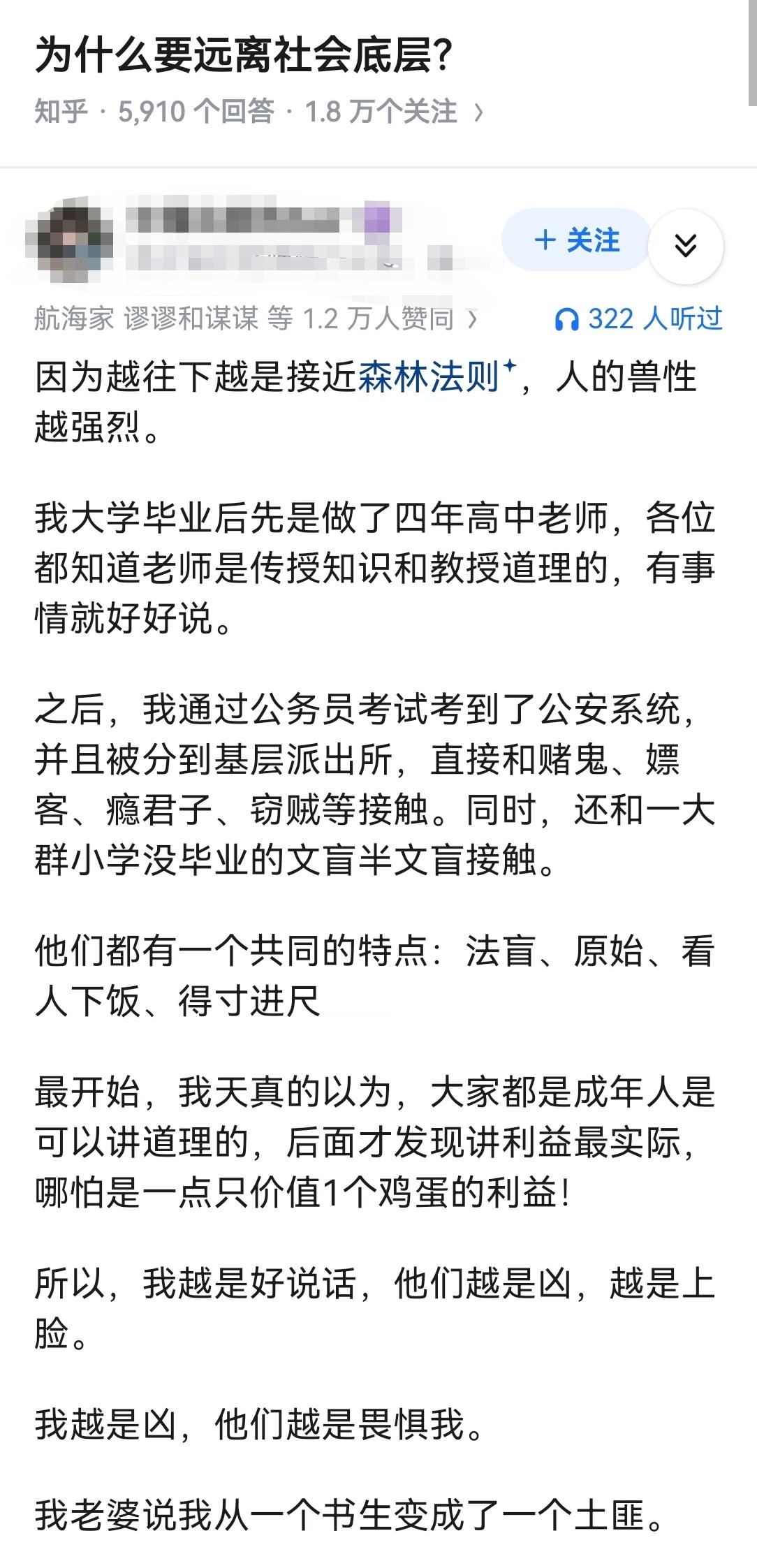1987年,河南一位考古专家,将一块甲骨放大了10倍,无法相信眼前一幕,竟然看到龟甲上,好像一只眼睛在向他眨眼,他仔细再看后,忽然热泪盈眶大呼:找到了,终于找到了! 当你透过十倍放大镜凝视一片破碎的龟甲,上面那个仿佛在眨眼的刻痕,不仅仅是一个记号,更像是一次穿越七千多年的对视,这就是在河南贾湖遗址发生的震撼一幕:考古专家在昏黄的灯光下,原本以为自己眼花眩晕,晃了晃头再定睛细看。 那并非纹路的巧合,而是一个确凿无疑的眼睛状刻符,那一刻,不仅眼泪涌上眼眶,整个关于中华文明起源的时间轴,都在随着这个符号的出现而剧烈震荡,这种震荡并非夸大其词,长久以来,学术界特别是西方学者的认知里,中国的信史只能上溯到商代的殷墟。 因为那时候成熟的甲骨文体系(约公元前1200年)才是文明的确证,而这块龟甲以及随之出土的龟甲、骨器、陶片上多达十几种的契刻符号,经碳14精密检测,将那个刻画动作锁定在了距今7762年(±128年),也就是公元前5000年左右。 这个时间节点,直接比商代甲骨文早了近六千年,甚至在这个时间坐标上,它和传说中的“夏朝”有着微妙的重合,然而承认这些刻痕是“文字”,是一场跨越东西方观念的漫长博弈,争议的焦点在于“体系”与“载体”。 西方的评判标准深受苏美尔文明影响,在两河流域,西方考古学家挖出了成吨的楔形泥板,那个大约6000年前就进入城邦时代的苏美尔人,留下了清晰的文化脉络,比如在公元前4500年,苏美尔的大城市埃利都就已经拥有五千人口的规模。 更重要的是,他们保存下来了大量完整的《苏美尔王表》泥板坚硬且不易损耗,让西方学者习惯了“文字必须成批出现、成文记事”的铁律,相比之下,贾湖刻符显得太“孤单”了,西方学者常常摊手质疑。 你们发现的符号数量太少,且大多不成句段,也许只是古人刻着玩的星星、人脸,或者是一种类似月饼图案的特定寓意符号,怎么能叫文字,这正是中华文明探源中最痛心也最无奈的地方。并非我们的祖先不书写,而是因为我们的“载体”和“际遇”太过坎坷。 早在殷商之前,古人可能广泛使用过草木、结绳来记事,这些材质根本无法穿越几千年的时光,更遗憾的是,贾湖遗址发现的刻符之所以只有区区十几个,很大原因归咎于后世对“龙骨”的迷信,无数承载着远古文明密码的龟甲。 被当成了药材吞进肚子,彻底消融在历史的胃液里,幸亏商人有着“无事不占”的繁琐习俗,才让殷墟那些占卜用的甲骨得以海量封存,但越是深入比对,专家们越有底气,这些七千年前的刻符,绝非随意的涂鸦。 当把它们放大,拿来和数千年后的甲骨文并排放在一起时,那种惊人的血缘关系无法掩盖:从笔画的走势到结构的布局,贾湖刻符像极了甲骨文的“前身”不仅如此,考古视野扩大到全国,我们看到了一个绵延的“文字孕育期”。 在大汶口发现的陶尊符号、山西陶寺遗址朱书扁壶上那个疑似“易文”的朱砂红字、甘肃大地湾那早已存在的彩绘符号,都在无声地拼凑一张庞大的文明拼图,这种连续性是中华文明独有的韧性。 文字的产生从来不是孤立的烟火,它必然伴随着复杂的社会需求,试想一下,在同一个贾湖遗址,我们挖掘出了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骨笛,发现了酿造精良的贾湖酒,看到了房屋基址和精细的墓葬分工。 一个在音乐、享乐、手工业和贸易分工都达到如此高度的族群,如果完全没有一套记录符号来进行管理和交流,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更何况,史书里大禹治水的记载中,面对滔天洪水,若没有各部落强有力的协调统一,若没有高效的信息传递。 涂山氏等各部族如何能“齐心协力”疏通江河,夏朝的建立依托于这种极高的威信与社会组织力,而文字,就是其中最关键的粘合剂,故宫博物院的专家们如今倾向于认为,从贾湖的“眼睛”到良渚的符号,再到半坡、陶寺的刻画,这是一条从未断裂的河流。 它们或许还不能完全讲述一个完整的故事,但它们填补了甲骨文之前那段漫长的空白,不像古埃及或苏美尔文明那样在历史长河中最终断层、消逝,中国的文字像一颗顽强的种子,虽然早期的一段根系深埋泥土难以全貌示人。 但它确凿地在这片土地上生长了数千年,生生不息,那个七千年前刻在龟甲上的眼神,其实一直都在注视着后人,等待着我们读懂它的那天。 信息来源:漯河日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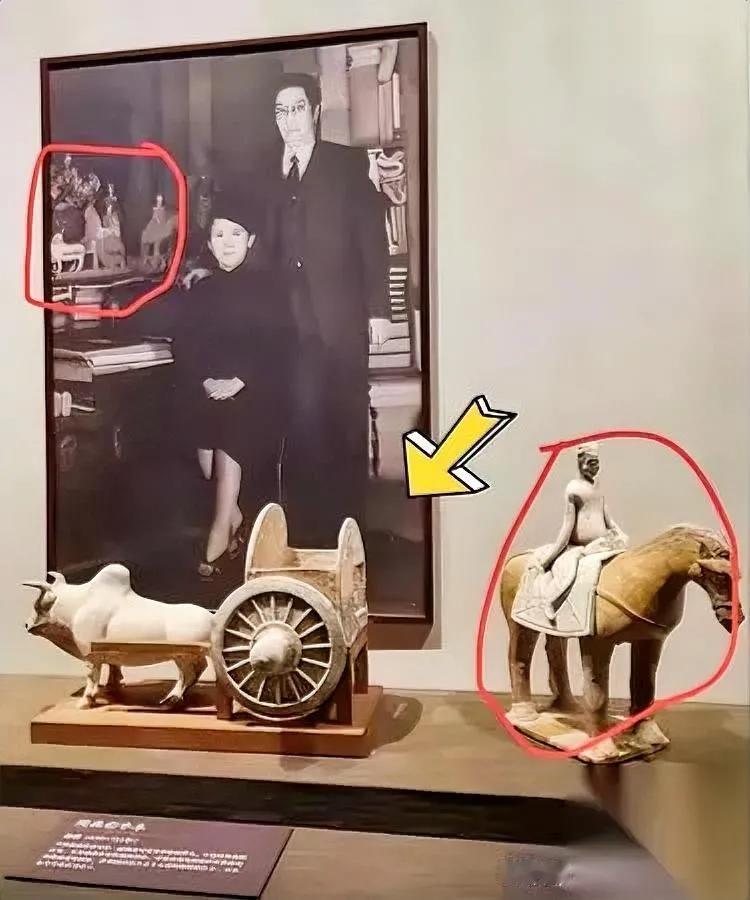
![人们的思想变了,即使白送一套房都不行[汗]](http://image.uczzd.cn/17539162800797291716.jpg?id=0)